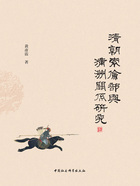
三 关外八旗研究状况
八旗研究是清史、满洲史研究的重中之重。自从20世纪30年代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实》发轫以来,有关八旗问题研究的论著便一发不可收拾,尤以王锺翰先生的《清史杂考》《清史余考》《清史续考》《清史补考》之清史“四考”为著。近四十年来,八旗研究的成果不可胜数,但是与禁旅八旗(京旗)、关内驻防八旗相比,从关外八旗内部民族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还显薄弱。
定宜庄研究员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32]是研究驻防八旗的首部专著,严格地说该书是作者《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33]的修订版。书中将关外与天山南北、内外蒙古(包括察哈尔)的八旗驻防归为北部边疆驻防,与直省驻防、长城沿线驻防鼎足而立,具有北抗沙俄边疆前线和祖宗发祥战略后方的双重意义。作者提出索伦牛录从结构或职能上,均与八旗牛录不同,而与清朝在东北建立的噶栅组织类似,是一种编户政策。[34]并明确提出,布特哈八旗不是新满洲[35],人们经常混淆这两个概念。清代中期以后,北部边疆少数民族部落兵在清朝国家统一的历史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胜于各直省驻防八旗。[36]而索伦、达斡尔兵丁所得半俸半饷与京旗、直省驻防八旗相比,实为不公正之待遇。而迁徙到伊犁的索伦、达斡尔兵丁直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才得以享受全饷,这是满洲统治者对其远离家乡、戍边卫国的肯定。
孙守朋教授的《汉军旗人官员与清代政治研究》[37]视角独特,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八旗汉军的专著。该书从八旗汉军官员群体入手,探讨汉军官员的历史作用、清朝统治者对汉军官员的态度与政策、汉军官缺设置等问题,重点关注乾隆朝以前督抚、驻防将军这一层次的汉军封疆大吏,以求阐述汉军官员势力的形成和发展变化。该书有采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清朝官员可分为四大群体,即满洲官员、蒙古官员、汉军官员和汉人官员,一般来讲,其地位按顺序由高到低。作者没有孤立地写汉军旗人官员,而是将其放在清史的背景中,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与满洲官员和汉官进行比较。该书把汉军官员与其他三类官员进行了官缺、待遇等方面的比较,从横向上突出了汉军官员身份地位的特殊性。尤其是汉军官员介于满官、汉官之间,彼此密切关联,所以理清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了解汉军官员地位的确定与变化、整个群体势力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作者深入透彻地研究汉军旗人官制。第一,剖析汉军旗人的族群意识。八旗组织可以被视为一个族群。这个族群的边界,不是地理边界而主要是社会边界。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可以通过服饰、语言、生活方式来区别于其他群体,从而认同自己的群体。清代“不分满汉,但问旗民”,这不仅说明在物质待遇上旗人高于民人,还说明在居住地域、生活方式上旗人和民人也截然不同。旗人长期居住在一起,文化日益接近,在共同的利益支配下,必然会在心理上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从而培养出共同的感情。汉军旗人的族群认同在汉军旗人官员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譬如,高宗编纂《贰臣传》将清初降清的汉官汉将列为贰臣,严重伤害了汉军旗人官员的感情,对于民族关系的维系、政权的巩固,无疑起到了负面作用。另如,圣祖所说的三藩“撤亦反,不撤亦反”,论证三藩反清之必然。其实不撤藩,不触动藩主的根本利益,“未必反,撤藩未必都反”[38]。吴三桂等汉官汉将的反叛亦给后人留下了推证的空间。第二,洞悉包衣势力对汉军官员势力的冲击。包衣与汉军原系两类旗下人,两类人的任职本不相同,包衣的任职本对汉军官员没有影响。但是到雍正、乾隆时期情况有所变化。“雍正朝和乾隆朝,包衣势力的发展对汉军官员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两项规定上:一是包衣与汉军一起补汉缺,二是乾隆三年(1738)规定,包衣归汉军额内考试”[39],从而造成汉军就职者减少,汉军官员势力的下降。第三,深化汉军出旗问题的研究。汉军出旗问题,以往学界多泛泛而谈,但该书深入探讨了汉军官员出旗的缘由和过程以及影响,把汉军出旗问题研究引向深入。书中讨论了汉军六品以下职官出旗反复现象。早在雍正五年(1727)“汉军闲散人丁如果情愿加入绿营,根据申请程序,可以入民籍而出旗;停止旗人作外省驿丞、典史等杂职,原则上令回旗,当然也包括即使汉军微员也不准出旗为民”[40]。到乾隆七年(1742)四月,规定“改归民籍世职者,仍许其带往,一体承袭;自愿出旗的汉军官员与所有出旗者一样‘俱限一年内具呈本管查奏’”[41],汉军出旗政策是逐步放开的。从乾隆二十七年(1762)开始实行汉军六品以下官员自愿出旗的政策,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停止汉军六品以下职官出旗。书中还研究了驻防汉军官员的出旗或调补。“在京八旗汉军官员六品以下官员是自愿出旗,而驻防汉军官员离职是强制性的,出旗或到京候缺。汉军官员出旗或调京总体来看是顺利的,没有产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骚乱,这与清廷政策引导和地方官员妥善办理有直接关系。”“驻防汉军官员出旗,直接导致了汉军官员数量减少,一部分回京候补,造成官员壅滞,汉军官员升转困难。”[42]这就使汉军出旗问题的研究愈加深入而具体。
孙进己、冯永谦总纂的《东北历史地理》(下)[43]将明清东北民族和建置的分布条分缕析,其中有明代后期女真三大部和索伦部的分布,清代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分布,经清朝整合黑龙江沿岸各族之后的八旗驻防状况,鄂温克人、鄂伦春人、达斡尔人的佐领十分详细,很有价值。
韩狄的《清代八旗索伦部研究——以东北地区为中心》[44]是第一部以索伦部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对索伦部各个时期的变化和史事做了系统研究,将索伦部的发展放到清朝统治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时间线索清晰,详述索伦部在黑龙江北时期的状况,南迁嫩江流域编入黑龙江驻防八旗,由“八围”编为布特哈八旗、呼伦贝尔八旗、伊犁索伦营,近代索伦、达斡尔、鄂伦春人的社会生活,以及索伦部与满洲的文化融合。
金鑫的《八旗制度与清代前期索伦达呼尔社会》[45]是篇史料厚重的博士论文,充分利用《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将明末清初到乾隆朝的索伦、达斡尔人在八旗制度管理下的社会生活、军事活动予以详细探究。
刁书仁的《清代八旗驻防与东北社会变迁》[46]首章详述清代东北八旗驻防体制,作者多年研究东北史,条分缕析,在考察黑龙江驻防八旗形成的过程中,注意职官的设置,黑龙江、墨尔根、齐齐哈尔分别设置副都统,呼伦贝尔、布特哈分别设置总管(副都统衔)。该书在写作八旗驻防制时,明确将“布特哈八旗”“新满洲”“巴尔虎旗”“锡伯兵”并列推出,厘清这几个概念的边界,与定宜庄研究员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说法相同。徐凯根据《八旗通志》也将索伦与新满洲区分开来。[47]
潘洪钢的《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社会变迁》[48]对东北八旗驻防也有涉猎,跟关内旗城相比,东北八旗驻防城市有其特殊性,即没有置身于汉族的汪洋大海中,成为“方言岛”。但从材料的丰富程度来看,东北旗城的材料相对于关内旗城则少得多。清末新政时期新军的建立成为取代东北八旗驻防的军事力量,“东北从旗制管理体系转向了内地的省区管理体制”[49]。而黑龙江省地广人稀,驻防旗人可以务农,结合畜牧渔猎,境遇较关内旗人优惠很多。吉林省驻防中的渔猎部落赫哲等,原不耕种,也拨给成片土地。东北三省是旗制改革最彻底的地区,从旗民双重管理体制改变为行省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