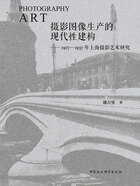
序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图像生产如此活跃,如此重要。在图像文化异军突起的背后,数字技术是强有力的推手,它不仅改变图像的形态和生产传播方式,也不断扩大图像的用途。但技术对图像的造就,并不是从数字化时代才开始的,20世纪初,摄影技术和机器复制技术开启图像生产的繁荣,是视觉文化和视觉艺术第一次遭遇现代科技和工业化的洗礼。从技术、文化、美学交织的角度追溯摄影的历史,既是拓展摄影研究的学术空间,也是重现图像史完整链条的一次努力。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混杂着新异与古旧,浮华与贫瘠,有直追国际新潮的思想文化、生活时尚,亦有芸芸众生的挣扎与坚韧。那个时代的多样性,凭借初出茅庐的摄影艺术留下了珍贵的影像。从社会与艺术交织的角度,探讨摄影图像生产的现代性维度,无论是对于理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还是对于理解视觉艺术的现代性建构,都是一个有趣且富含理论意义的切入点。
潘万里对1927—1937十年间上海摄影艺术的研究,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展现了洞察力。作为一项立足于多学科交叉点而推出的成果,《摄影图像生产的现代性建构》试图突破和修正现有摄影史研究范式,一方面强调摄影史研究需要提升理论高度,把个案分析、历史考察纳入对中国摄影艺术理论和摄影美学的研究;一方面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打破“摄影本体主义”的思维模式,将十年繁荣期上海摄影艺术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文化消费以及政治意识建构相勾联,史论结合,分析摄影如何在现代中国的视觉文化中发挥重要的建构性作用。思维上的解缚,使之在这一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中国本土摄影的起点问题;“画意摄影”概念的泛化和混用而导致的认知偏误问题;本土现代摄影艺术所探索的媒介自律问题;摄影的审美范式演变问题;民族志纪实摄影重塑国族认同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解答,自然还需进一步展开、完善,本书的完成,肯定不是研究的终点,但这些问题的提出,无疑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而精彩的探索空间。
《摄影图像生产的现代性建构》的底本是潘万里的博士论文。2015年,潘万里考入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随我攻读艺术学理论博士学位,好学多思是我对他的总体印象。我们的讨论,常常从课堂持续到课下,师生三五人,沿着校园小径,议题也一路延伸,其中,潘万里通常是思维最活跃,发言最积极的那一个。我任教至今,一直认为对人文学科的教育而言,面对面的交流,各出所见,相互辩诘,是必不可少,也是极富成效的方式;而学生充满锐气、闪现灵感的反馈,也是身为教师最大的快乐。当年论文答辩前夕,我告诉潘万里论文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今次成书,修改提升之处,已颇有可观。学海无涯,惟愿这位扬帆启程的青年学人不负时光,阅历与年岁同长,学问随阅历益增。
马睿
2020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