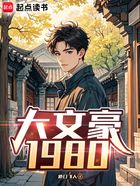
第4章 《十八岁出门远行》与平庸之恶
今天是星期日,终于熬到了休息,赵健康一早就来敲门,找张盐去钓鱼。
张盐回忆了原来他和赵健康钓鱼的经历,十次有九次是空手而归,遂悠悠道:“我就不去了,外面卖的鱼到了晚上就不新鲜了。”
主要张盐今天已经有了计划,难得有连片的休息时间,他打算写点东西出来。不然他也挺愿意去体验一下没有各种高级装备的老式钓法的。
一旁的张绛说,赵哥,我!我去!我跟你钓!
赵健康白了张盐一眼,信誓旦旦地说:“走,你哥不去没关系,咱哥俩去,今天我就是你亲哥,我们把玄武湖的鱼钓光!”然后拎着个根竹竿带着张绛走了,背影像个空军。
张慈瑞还在忙那起分尸案,案子虽然确定了嫌疑人,但找人又何其难,尤其是没有天网的时代,即便有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但大海捞针也是需要耗费极大精力的,他整个人都憔悴了不少,一早就去了派出所。
谢兰系着围裙,看到张盐坐在书桌前吊儿郎当地转着钢笔,迅速进入角色:“起来了被子也不知道叠,怎么这么懒!你看看你都多大了,还不赶紧找个对象结婚,你看隔壁的魏刚,人和你一般大吧,孩子都有啦!你什么时候能给我抱个孙子回来,我看小巧就不错,你们还拖什么呢......”
张盐打哈哈应付着,一边说好的好的,一边把谢兰女士推出了房间。
“......我还没说完呢,你要听啊!别不当回事!”谢兰看儿子似乎真的想写点东西,也就借势离开了房间。
大儿子远在战场,二儿子殒命,小儿子还不通人事,女儿出嫁。身边只有三儿子愿意听她说说话,谢兰还是很珍惜和儿子相处的时间的,对她来说,家庭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儿子想写,就让他写吧,最多浪费点稿纸。
在谢兰眼中写作等于浪费稿纸的张盐将稿纸摊开,英雄329钢笔已经吸满了墨水,拔掉笔帽,犹豫了片刻,一行不怎么好看的字出现在了张盐手下的黑白格子中:
《十八岁出门远行》
这是余桦的成名之作,87年发表在《京城文艺》上,篇幅很短,只有不到5000字,用一个半天就可以写完。
故事结构也很简单,就是一个十八岁的男孩初次出门远行所经历的生活片段组合,连贯性不强,故事性也不强,但却是张盐除了《在细雨中呼喊》之外,最喜欢的一部余桦作品。
在这篇小说中,一个满怀憧憬的少年离开家乡踏上冒险之旅,他偶遇一位卡车司机,殷勤递烟示好却被冷脸驱赶,直到车轮故障时少年主动协助修理才被允许搭车。车厢颠簸中,少年将司机视作旅途知己,兴奋地倾诉自己对远方的想象。
命运骤然转折——卡车半途抛锚之际,成群路人如嗅到血腥的秃鹫般围拢,嬉笑着将车斗的苹果哄抢一空。少年目睹暴行挺身怒斥,却被暴徒殴打得遍体鳞伤。荒诞的是,本该同仇敌忾的司机非但漠视少年的正义,反而从对方的惨状中滋生出扭曲的快意,最终加入了抢劫少年的队伍中,夺走少年仅有的行囊,成为压垮少年纯真世界的最后一根稻草。
小说结尾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是,父亲对少年说:“你已经十八了,你应该去认识一下外面的世界了。”
张盐欣赏这部作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最后的这一句话。
在后世东国的很多作家里,描写人性之恶的有许多人,如管莫言笔下最贴近原始的暴力野蛮,阎涟科关于极端生存环境下的道德溃败,苏瞳笔下的关于江南的阴郁欺凌,但这些描写都太聚焦于某一个点,而不够概括和普遍,相较之下,余桦的洞察则更为深刻和冷峻。
认识外面的世界,就是认识外面世界的多元和复杂,《十八岁出门远行》这部作品里没有杀人放火强(暴(虐(杀,只有着连绵不绝的小恶,看到别人抢苹果,于是自己也加入,司机不能回击欺辱他的人,只能反过来欺辱更弱小的少年......这些小恶才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像是米饭里的砂石,就像是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
1961年,汉娜·阿伦特在观察以色列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庭审中发现,恶的施行者并非传统认知中“邪恶的犯罪天才”,而是一个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机械服从的普通人。战犯艾希曼在法庭上反复强调自己“只是执行命令”,其行为的动机并非个人仇恨或狂热,而是对程序与命令的盲目遵从。“平庸之恶”并非指罪行本身的轻微,而是指作恶者精神上的肤浅与无反思性。战犯艾希曼的“平庸”体现为一种“无思想的行动”,即放弃对善恶的判断,成为某种机器的“齿轮”。
阿伦特晚年将“思考”提升为对抗恶的核心力量。她认为,思考并非获取知识,而是通过“与自我对话”保持对现实的清醒认知。这种思考不是哲学家的特权,而是每个人的责任。
正如她所言,思考的缺席可能使普通人成为恶行的执行者,而思考的微光足以在黑暗中开辟救赎之路......
从这个角度来看,余桦作为一个文学家,同时也完成了哲学家的任务......
张盐写的很是起劲,他越写越发觉自己记忆力的提升,他竟然能记起不少原文原句,这也许就是穿越的福利吧,如果早有这种记忆力,恐怕自己也能上个京师大......
余桦在写作这部作品时,还很青涩,有些片段的处理并不连贯,更像是碎片的拼接而不像一部小说。
因此,张盐在写作时,作了修改,在内核不变的情况下,他增加了小说的故事性,调整了一些细节以更加符合当时时代的特点,以及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自认为),加了司机的心理描写......
......从清晨写到中午,张盐已经完成了一半,肚子也饿的咕咕叫,正准备出去看看谢兰弄了哪些吃的,还没出门,就听到谢兰欣喜洪亮的声音:
“小巧,你来就来,怎么还带东西,阿姨能饿着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