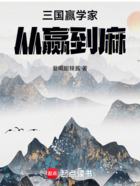
第58章 相信后来皇帝的智慧
洛阳城北,太学。
黄庸再次踏入这片既熟悉又疏离的土地,这里曾是汉家最高学府,如今虽冠着曹魏最高学府的名号,却早已不复往日荣光,九品官人法之下,太学已经完全丧失作用,世家子弟对此地不屑一顾,太学渐渐沦为躲避兵役者和混日子的失意人的聚集地。
黄庸一袭青衫,姿态从容,穿行在稀疏的人群中。
周围的太学同学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或高声谈笑,或低头私语,神情轻佻,毫无对这学府的敬畏,更多的是市井间的油滑与无聊。
黄庸目不斜视,径直走向那片象征着太学最后尊严的所在——熹平石经碑林。
高大的石碑如同沉默的巨人,静立在午后的阳光下。
碑身上镌刻的经文,字迹或清晰或模糊,无声地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与今日的寂寥。
阳光透过碑林的缝隙,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浮动着淡淡的土香、石尘以及一种被时光遗忘的陈旧气息。
太学博士、大儒乐详早已等候在那里。
这位须发皆白的老者,是太学中少数几位真正将传道授业视为己任的博士。
他穿着一身洗得有些发白的儒袍,身形清瘦,眼神中却透着一股与这没落之地格格不入的执拗与热忱,看到黄庸走近,乐详原本略带呆滞的脸上飞快地生动起来,绽放出欣慰的笑容。
“德和,你来了。”乐详的声音带着长者特有的温厚。
黄庸快走几步,恭敬地深揖一礼:
“学生黄庸,拜见老师,这些日子学生波折不断,荒废学业,还请老师恕罪。”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乐详连忙上前虚扶一把,拉着黄庸的手臂,仔细打量着他,确定爱徒无事,他这才松了口气,轻轻拂了拂他的肩头,邀他一同在碑林间缓缓踱步,“你不在的这几日,为师在这学堂教起来也索然无味啊……哎,为师本事低微,知道你无辜入狱,也多多活动,却……哎。”
他叹了口气,目光扫过不远处几个勾肩搭背、嬉笑打闹的学生,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声音中充满了掩饰不住的失望:
“你看看他们,哪里还有半分求学的样子?
圣人经典在前,他们却视若无睹,整日里只知道聚在一起,传播些市井之间的污言秽语!真是……真是令人痛心疾首!”
当年熹平石经落成的时候,这里车水马龙,来的都是有志于学的儒生,现在太学荒废,此处也变成了这群虫豸聚会、踏青的所在,哪有曾经的半分荣光。
这些话乐详平日懒得说给这些虫豸,难得黄庸回来,他一时控制不住,飞快地道:
“想当初,孝桓、孝灵之世,太学何等兴盛!
天下英才云集于此,辩论经义,探究大道,针砭时弊,激扬文字!那才是读书人该有的模样!
也不知道老夫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看到儒道大昌的模样了。”
黄庸适时地沉默静听,等老师的情绪稍稍平复,这才适时开口安慰道:
“老师也无需太过忧虑。
天子的身子愈发不和,等平原王殿下登基,定会拨乱反正,重振文教。
有老师与高堂公这般人物兴教,太学再兴,或指日可待矣。”
这已经不是黄庸第一次说起这话。
事实上,从黄初五年开始,高堂隆、乐详这些受命修复石经的大儒每次走到此处都会长吁短叹,黄庸这话已经车轱辘一般反复说了不知道多少遍。
每次,乐详都会稍稍振奋起来。
但随即看着太学这些虫豸,这位年事已高的大儒又会慢慢痛苦绝望,渐渐意志消沉。
充当精神氮泵的黄庸不厌其烦地给老师打气,不只是老师乐详,还有高堂隆、苏林等人。
一群饱学大儒这几年来一直被黄庸反复打气,他们眼前的希望都聚焦在一起。
曹叡登基就是一道光。
尽管他们知道,九品官人法已经深入了大魏的根骨、魂魄,可黄庸这些年一直在给他们希望和情绪价值,只要提到“平原王”,这些压抑许久的大儒都会开心起来,对未来充满期待,迫不及待赶紧等来这一天,好一展身手,将众多积弊尽数扫除,还大魏朗朗乾坤。
乐详也不例外。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又呢喃道:
“九品之法要是没了,大魏的积弊就能扫除了,对吧?”
“一定,沉疴需要猛药,咱们太学日后,定是这般猛药。”
黄庸觉得自己没有说谎。
火化是包治百病的神医之术,如果发论文,能明显做到比对照组更好的实验效果,理论上是说的过去的。
他们的目标只是动摇九品官人法,这在未来也被证明是顺应历史的正道,至于大魏的躯干筋骨如何那就不是他们要考虑的。
相信以后皇帝的智慧吧。
黄庸的聊天术法给的情绪价值很高,乐详明显开心起来,两人在碑林中又绕了几步,乐详这才眷恋不舍得返回。
路上看见那些混日子的太学生又在三三两两地聚众闲话,乐详恨铁不成钢地摇了摇头,嘟囔道:
“这些人,要是再有三两个如德和一般,我也不至于这些日子如此劳心。
你听说了吗,这些鼠辈居然三三两两,说起宫闱私事,还胡言乱语中伤司马叔达。
也不知这谣言到底是何人编出,这些人连此事都信,真是岂有此理。”
黄庸哦了一声,老脸一红,又笑呵呵地道:
“此事我也听过了,可是……可是司马叔达与郭皇后之事?”
乐详沉重地点了点头,不愿相信自己教了这么久的书,这些畜生不学就算了,居然还在太学这种庄重肃穆的地方聊这个,真是让老人家心痛万分。
黄庸也沉重地点了点头:
“吾辈太学学子,每每谈及此事也当真不妥。
司马叔达清正,只是一贯低调,不为人知,横竖这些人也听不惯圣人学问,老师何不讲些司马叔达经营地方为民谋事之事,告诉这些学子这才是清流名士,圣贤子弟所为。
若是他们还有些良心,也该自惭形秽,频频称颂其功,不敢妄自非议宫闱之事?”
乐详点了点头,心道可能自己的教育方法确实有点问题,不能像圣人一样因材施教。
黄庸的法子让乐详眼前一亮,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司马孚这样正直之臣,一直没什么非议,现有的非议居然是从太学开始,这让乐详觉得自己有责任好好教教这些不学无术的儒生。
毕竟他们都是出自寒门,很多人不了解司马叔达也是应该的,这些学子听不懂圣人的经义,我也该讲讲当世正道之士所为,这些他们哪怕能学到一二,对社稷也是功勋了。
乐详筹谋片刻,又道:
“不错,之前坊间亦有正直之士颂扬司马叔达治理沁水之功,我太学诸生应该学的便是这般为国为民之事,岂能每日讨论……哎……”
他又把目光对准黄庸,眼神里充满了期盼和感慨,“老夫真希望,大魏能有一百个黄德和,那该多好啊!”
黄庸微笑着欠身,心道司马孚治理沁水时在一处大兴土木,见那里朽烂不堪的木门枋不堪用,需要改造成石门阻挡洪水,这份功劳日后马上就要通过太学、通过诸事被天下人知晓。
能让司马孚这个在后世知名度不高的大魏纯臣多点画面,黄庸觉得自己真是为大魏考虑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