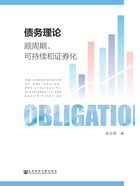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提出问题
进入21世纪的头十年,全球经济经历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在2008年的时候爆发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此次危机的波及范围之广、破坏程度之深令经济学家们惊呼“这次将不同于以往”(This Time Will be Different)(布拉佳、文斯利特,2014),以致多年后各大主要经济体仍未实现真正复苏。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15年共四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率的预估值,从年初预估的3.8%不断下调至后来预估的3.1%,而这一经济增长率的预估值创下了自本次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速的最低纪录(IMF,2015)。
更为糟糕的是,在经济增长乏力的同时,全球经济又重新开启了新一轮的“加杠杆”(Leveraging)过程,全球总体的债务余额(包括居民、非金融企业和政府部门,但不含金融机构的债务)占全球GDP的比重仍保持不断增长的态势,2016年达到234.8%,创下历史新高,相较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202.1%)大幅上升32.7个百分点,并且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都纷纷落入“债务陷阱”(Debt Trap)之中。以2016年的数据为例[1],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的负债率(年末债务余额/当年国内生产总值,以下同)高达264.5%[2],相较于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和21世纪初的2001年分别上升了24.8个百分点与52.7个百分点。其中,英国、欧元区和美国的负债率分别为280.4%、265.8%与252.9%,依次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增加了37.2个百分点、33.5个百分点与13.4个百分点,而相较于21世纪初的2001年更是上升了99.0个百分点、57.1个百分点与63.4个百分点。更有甚者,像日本在2013年的负债率竟然达到371.0%。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负债率为184.3%,虽然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水平,但也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上升了76.7个百分点。
对于中国而言,自后危机时期以来,债务水平的增长非常迅速。从总体的债务水平来看,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的总体负债率(不包括金融机构)为257%,比2008年大幅增加了116个百分点,年均增速超过14%,这一增幅不仅是同期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在已有数据披露的国家中,只有中国香港的增幅超过中国内地),而且也比危机之前美国的增长速度快。再者,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测算,截至2016年底,中国实体经济的债务规模(不包括金融机构)约为168.8万亿元,负债率从2008年的157%大幅上升至2016年的227%,年均增速超过10%(张晓晶、刘学良,2017;张晓晶、常欣,2017)。
从分部门的债务水平来看,按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计算,2016年底,我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余额高达17.79万亿美元,超过同期美国的水平(13.47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拥有未清偿的非金融企业债务最多的国家,并分别占到新兴市场经济体债务总和(25.68万亿美元)的69.3%、全球各国债务总和(62.10万亿美元)的28.6%,而同一时期的非金融企业负债率为166.3%,相比2006年的106.5%,累计上升了近60个百分点;2016年底,我国政府债务余额达4.96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8.36万亿美元)和日本(9.23万亿美元),但同期的负债率为46.4%,仍处在国际警戒线水平之内。国内的研究也显示,2016年我国非金融企业与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各为94.4万亿元、30.2万亿元,同年两者的负债率分别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上升了32个百分点和50个百分点(李扬、张晓晶、常欣,2015;张晓晶、刘学良,2017;张晓晶、常欣,2017)。
总之,上述多项国内外的统计数据均表明,当前中国快速攀升的债务水平必须引起各方的关注,特别是非金融企业与地方政府所隐含的债务风险更值得高度警惕。
有鉴于此,不管是反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还是抑制爆发下一次金融危机的风险,这些议题都不能脱离债务的分析框架来展开讨论。通过结合债务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不管是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以及随之蔓延至全球的2008年金融危机,还是2009年底在欧元区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抑或是当前中国非金融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隐忧等,一系列挑战的背后都有一个共性,那便是经济主体都有过度举债的情形。具体而言,在十分宽松的货币环境下,随着经济的好转,经济体中的各个部门都纷纷地采取顺周期性的“加杠杆”行为。可以看到,居民和非金融企业部门转而更偏好通过借债来进行消费与投资;金融机构则通过以证券化为代表的各种金融创新手段来积极支持前两者的举债行为,从而其自身也比以往显得更为稳健且赢利颇丰;政府也更为激进地安排看似短期内具有可持续性的财政支出和社会福利政策(莱茵哈特、罗格夫,2012;汉农,2015)。不过,最终的结果是债务按照其自身所具备的顺周期性、可持续性与证券化这三大特性的作用演变从而给整个经济体带来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并且之前由债务过度累积而催生的经济繁荣也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3]。为此,从债务的理论和实践出发,深入探讨债务的三大特性——顺周期性、可持续性与证券化,并结合中国现实和国际经验,这便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也正是基于迫切的理论和现实诉求,本书的研究旨在试图解答以下有关债务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
(1)“债”的起源是什么?“债”是如何演变的?“债务”的概念又是什么?“债务”具有哪些特性?
(2)“债务”的“顺周期性”是指什么?有哪些表现特征?通过何种作用机理来影响经济?结合中国现实,尤其是关于中国特色的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和商业银行经营模式,“债务”的“顺周期性”(以“银行信贷”为载体)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上分别是怎样表现的?
(3)“债务”的“可持续性”(以“政府债务”为载体)是指什么?“政府债务”具有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基于中国现实,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在跨期预算约束下的现状如何?未来有哪些挑战?借鉴国际经验,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具有怎样的宏观经济效应?如何有效控制由此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
(4)“债务”的“证券化”是指什么?有怎样的运作模式?通过何种传导机制来影响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介绍国际经验,对全球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状况进行考察,特别是对美国证券化市场在2007年次贷危机前后的发展变化有何启示?结合中国现实,“债务证券化”(以“影子银行体系”为载体)具有怎样的宏观经济效应?该效应所产生的原因何在?
围绕上述这些问题,笔者将以债务特性作为核心议题,分别从债务的顺周期性、可持续性与证券化这三大特性入手来展开具体研究,既总结国际上的经验和教训,又结合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通过理论建模和经验实证的分析方法,来全面、系统、细致且深入地考察债务在三大特性上与之一一对应的具体表现载体——银行信贷、政府债务和影子银行体系,最后提出各自行之有效的控制债务产生系统性风险的政策措施与应对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