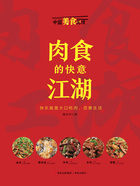
猪油美食和菜饭
猪油可暖心
猪肉是大部分中国人吃的数量最多的肉。大部分人家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就是用猪肉制作的各种菜肴。猪肉类菜肴虽多,但我觉得最能体现猪肉类菜肴风味的还属用猪油制作的各种美食。
在有机化工业里,猪油和牛油、羊油通常不被视作同一类材料。
牛油、羊油性状稳定,很适合用于工业制造。而猪油在天气热的时候,可能在室温下就会化开,而且性状不稳定。造成猪油性状不稳定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猪油里含有太多的杂质。

这些“杂质”,恰恰造就了猪油迷人而多变的香味。本质上来说,猪油香味的来源是猪肥肉炼制过程中析出的一部分芳香物。不需要加太多调料,猪油与各类食物的结合就能给人带来愉悦的感受。
南唐后主李煜这样描写江南的倒春寒:“罗衾不耐五更寒。”简单七个字,深刻而妥帖。春寒之夜,就需要来点儿暖胃暖心的消夜。加了白糖的红豆粥也许不错,但缺了油润;撒了胡椒、香菜的羊肉汤固然好,但缺少温和。一碗猪油菜饭,才算是初春之夜最妙的选择。

江浙沪猪油菜饭
猪油菜饭和蔡澜钟爱的猪油捞饭其实是两种东西。“捞”在广东话里有一个意思是“混合”。而钟爱猪油的广东人又有拿它和酱油、小葱花等一起拌白米饭吃的传统,所以猪油捞饭的核心应该是猪油而非其他。蔡澜说吃一口猪油捞饭,会激动到流泪。我想他拿猪油捞面、捞粉、捞一切可以捞的主食,应该都有一样的感受。
但猪油菜饭里的菜却是很重要的部分。这里的“菜”,特指小青菜,在江浙地区,也叫小棠菜、上海青、江门白菜。不同于适宜夏天吃、脆爽无比的小白菜,小青菜这东西不到秋天气温较低时就不肥厚,吃着也会有涩嘴的青草味。要等到霜打过后,肥美的菜梗基部膨大出微凸的小球时,才能出现甜味。上海人擅长拿它清炒,加点儿蒜蓉和盐,不用别的调料,就足够鲜甜。小青菜拿来煮食也不错,用它做的小青菜年糕汤尤其值得一书。上海小青菜、宁波年糕条、舟山大海米、苏州豆腐干一锅煮,再来点儿香油、小葱即可。吃后满嘴都是吴侬软语的甜糯喷香。
当然,若论小青菜最好的归宿,那必定是做成猪油菜饭。
2008年,上海世博会前夕,我在沪采访。彼时的“魔都”像个大工地。当天忙完已是夜里十点多,踟蹰街头,从人民广场一直走到老西门,实在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吃食。正准备在便利店买个盒饭随便打发,却忽然在东台路古玩市场外发现一家小馆子冒出热气。走进去后发现老板是操着一口上海话的本地人,菜牌上也都是排骨年糕、菜肉大馄饨、火腿菜泡饭等散发着“石库门风情”的东西。
我要了一份猪油菜饭,揭开黑魆魆的瓦钵盖,感觉一股混合着猪油香和蔬菜独有的清新味道的蒸汽扑面而来。这些味道让人打了个幸福的哆嗦。嗯,菜是正宗上海青,菜梗肥厚而叶片细小,闷在白米饭里,早已软糯适口。菜叶子的颜色或许卖相不好,但加了猪油之后油润的样子,依然让人胃口大开。配着一碗新冲的老油条紫菜汤,香、咸、甘、爽都齐了。那样的消夜,不适合细嚼慢咽,最好是狼吞虎咽,到肚里饭菜都是热的才好。到最后,恨不得把钵里的葱花碎都舔干净。
其实,沪式猪油菜饭和广式猪油捞饭,最大的不同应该是沪式讲究“热乎”两字。许多人不懂行,像做捞饭一样把猪油、酱油倒在菜饭上搅拌。如果是大冷天的话,那凉的就不只是“黄花菜”了,心也凉了——本来软糯的菜梗子,会变得糊烂,一如剩菜,无法入口。
咸肉菜饭
因为菜饭讲究的是“热乎”以及“菜”,所以猪油并不是菜饭的必选项。茹素者可以用花生油、芝麻油之类香味重的油来代替猪油。而作为菜饭里高阶版本的咸肉菜饭,当然也是不放猪油的。我曾经在和平饭店能望到黄浦江的包间里吃过一顿非常精致的咸肉菜饭。它用的是腌制、风干的五花肉。厨师刀工了得,将肉切成薄薄的片儿,而且每一片都有皮、有瘦肉、有肥肉。焖制过的腌肥肉是最好吃的,呈半透明的琥珀色,不腻,很香;米饭用的是泰国茉莉香,白口吃就不错;小青菜的处理最有门道,菜梗和菜叶子是分开的,菜梗切成小拇指粗细的条儿,和肉、饭一起焖透,快起锅时再撒入切碎的菜叶子,略焖即可。这样既能保证小青菜软糯入味,又增加了翠绿的颜色,讲究!
有朋友旅居澳大利亚,她告诉我,当地也有上海青——他们叫作“bak-choy”——可惜没有南风肉(一种腌制的猪肉),不能做咸肉菜饭吃。我说:“拿培根来代替如何?”试验之后,果然成功。超市的培根大多是片好的,连片肉的刀工都不用了,焖好后一屋子浓浓的烟熏香味。培根菜饭比上海街头许多人做的“咸肉菜饭骨头汤”好吃无数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