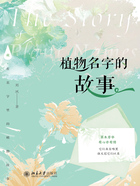
引言 理解草木之名
一点也不夸张地说,人类之所以贵为万灵之长,就是因为他们会起名字。
东汉有个大学问家叫许慎,他编了一本书叫《说文解字》,是中国最早的字典。这部巨著有一点让我很不满意——里面竟然没有收我的姓氏“刘(劉)”字。后人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说是避讳,有人说是写成了另一个字,但不管怎样,反正是没有收这个字。
不过,我个人的一点不满,当然不能掩盖这部书在揭示汉字字源上的重大成就。比如“名”这个字,上面是个“夕”,下面是个“口”。“夕”的本义是傍晚,那么名字和傍晚又有什么关系呢?许慎为我们揭开了其中的奥秘:“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从口自名。”这意思是说,白天人们彼此能够看见,所以不需要称呼自己的名字也能让人知道你是谁。可是到了太阳落山之后,彼此就看不见了,要想让别人知道你是谁,就只能从嘴里喊出自己的名字。所以,“名”就是在“夕”阳落山后从“口”中说出的东西。
当我们从认知科学的高度审视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不同时,“名”这个汉字体现的造字智慧就已让人佩服不已。假定人类和其他所有动物一起进行一场智力竞赛,第一关是“推理”测试——如果A大于B,B大于C,那么A和C的关系如何?其实,光在这一关,比鱼类低级的所有动物都会被淘汰出局。
第二关则是“自我意识”测试,就是看能不能认出镜子中的形象是自己。看起来这也是很简单的任务,然而能够通过这一关的选手,除了人类之外,就只剩猩猩、黑猩猩、大猩猩、海豚、亚洲象和喜鹊(对,就是那种老是“嘎嘎嘎”地吵得人心烦的鸟)等少数动物了。
现在,关键的第三关来了:你是否能够把你意识里的世界分解成一个个的概念,并用语言表述出来?这一回,只有人类,以及受过人类训练的几只黑猩猩、大猩猩通过了测试。而当裁判再问:你能够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使用语言吗?那几只被人类教会了“符号语言”的类人猿便也败下阵来。最终,靠着卓越的语言能力——能够自由、随意地运用语词表达心中各种概念的能力——人类夺得了这场动物智力竞赛的冠军。
所以,不要小瞧我们起名字的本领。哪怕是我们随口管一个人叫“高个儿”,管另一个人叫“胖子”,我们都是在动用所有动物智力中最高级的技能——用语言表达概念。这个多少能够令我们感到骄傲的事实,就隐含在“名”这个字“从夕,从口”的字形里。
可是,当我们放眼打量大千世界的时候,实在是不能不叹息:这世界实在太复杂了,能够起名字的事物实在是太多了!难怪在任何一本一般的词典里,数目最多的词语总是名词——就是用来表达事物名字的词。
我手头有一本《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我随手一翻,翻到了第245页。这一页上共有44个词条(从“大赛”到“大团圆”),其中标为“名词”的就有28个,足足占到了六成多。在这28个名词中,又有不少是指称具体的、非抽象的事物——比如“大嫂”是“大哥的妻子”,或用来“尊称年纪跟自己相仿的已婚妇女”;“大少爷”是“指好逸恶劳、挥霍浪费的青年男子”;“大暑”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大提琴”是“提琴的一种”;“大头菜”则是一种“二年生草本植物”“根主要供腌渍食用”。
现在的很多箱包和衣服上都有“魔术贴”,一面是坚硬的钩状物,一面是柔软的毛绒,两面按在一起,就可以牢牢地黏住。我们从医院或药店买的药片、胶囊,很多是装在透明塑料板上面一个一个的凹槽里,这种带有水泡状凹槽的塑料板的大名叫作“泡罩”。对于“魔术贴”和“泡罩”,我翻遍《现代汉语词典》,既没有找到这两个词,也没有找到指称这两种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的其他名词。
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已经如此丰富多彩,可是比起大自然本身的多样性来,那又是小巫见大巫。就拿生物来说吧,现在,科学家已经为将近200万种的生物命了名;据估计,地球上现在还有生存的生物至少有2000万种;如果算上在几十亿年的历史长河中已经灭绝的生物,那么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生物的数目将超过1亿种!
在形形色色的生物中,有一类低调的生物叫作“植物”。大约十几亿年前,一个在水中游来游去、靠吞噬其他生物为生的单细胞生物,吞掉了一个蓝细菌(旧称蓝藻)。神奇的是,这个蓝细菌没有像其他不幸的猎物一样被马上消化,而是在这个吞噬者体内活了下来。最后,二者便形成了紧密的“内共生”关系——吞噬者为蓝细菌提供保护,而蓝细菌则把自己通过光合作用制造的养分分享给吞噬者。久而久之,蓝细菌成了叶绿体,而吞噬者也摇身一变,成了靠叶绿体给自己制造养分的“自养生物”。
按照今天科学界的最新定义,植物就是这个发生了“内共生”的古老单细胞生物全部后代的统称,其中大部分仍然像祖先一样,通过叶绿体来进行光合作用,自己养活自己(当然,例外也是很多的。如果你问我菟丝子这样不含叶绿素、不能进行光合作用的怪物是不是植物,我当然也会说“是”)。植物可以分为隐藻、灰藻、红藻、绿色植物4大类;绿色植物又分绿藻、苔藓植物、石松植物、蕨类植物和种子植物5类,其中能够结出种子的种子植物数目最多,全世界大概有30多万种。

|《中国植物志》第一卷封面|
尽管这个数目远远比不上全世界昆虫的数目(据估计有1000万种,占所有现存生物种类的一半),但也已经相当可观了。按照已经在2004年全部出版完毕的《中国植物志》,中国有种子植物将近3万种,是世界上种子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即使在我曾经居住的面积只有一万多平方千米的北京市,野生的种子植物也多达1700余种——把它们的名字列成表打印出来,需要好几十页纸。
我们都有这样的感受,有些名字对我们来说只是名字,而有些名字却承载了更多的信息。也许它能让我们产生喜怒哀乐的情绪,也许它能勾起一段遥远的记忆,很多时候,简简单单一个名字就能让我们浮想联翩,久久不能自已。
比如说,“桧”就是这样一个承载了丰富意思的名字。它最早的时候只是指一种树木,就是今天我们叫作“桧(guì)柏”或“圆柏”的常见园林和绿化树种。在春秋时代,“桧”也是一个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境内的诸侯国“郐”(kuài)国的别名。有人怀疑这个国名正是来自那里的山上生长的茂密桧柏树。《诗经》中有“十五国风”,其中就有“桧风”,虽然只收录了4首诗,却足以使小小的桧国和秦、晋(唐)、卫、郑这样的大国并列了。《左传》记载,吴国的季札曾经在鲁国观看以《诗经》为歌词的乐舞,他对各诸侯国的乐曲都发表了意见,可是从桧国的乐舞开始,却不再评论了。从此,汉语中就多了一个成语叫“自桧(郐)以下”,意思是由此开始的人或事物的水平就不足以让人再高看了。
也许这样一个带有贬义的成语,注定了“桧”这个名字会有更多的磨难。北宋末年,一位名叫秦敏学的小官僚按照当时流行的五行命名法,给自己的儿子起了这个带木字旁的名字“桧”。谁也想不到,这个叫秦桧(huì)的人后来竟然成了南宋大臣,但不幸的是,这是一个因卖国求荣、害死爱国将领岳飞而遗臭万年的奸臣。从此,“桧”这个名字就再也洗不脱身上的晦气了——清代有一位叫秦大士的状元,在拜谒杭州岳王庙时,就留下了“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的名句。

|圆柏,古名“桧”|
巧合的是,在德国人中,阿道夫(Adolf)这个名字享受到了同样的冷遇。它来自古德语Athalwolf一词,意思是“高贵的狼”。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阿道夫是德国男性中一个非常常见的名字。在植物分类学史上鼎鼎有名的阿道夫·恩格勒(Adolf Engler)就叫这个名字。然而,一切都因为一个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改变了——他创建了第三帝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把德国乃至世界都带入了灾难之中。当1945年希特勒自杀、二战结束之后,再也没有几个德国人愿意给男孩子取名阿道夫了。不过,这个和邪恶的法西斯主义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名字,直到今天仍然以变体“阿迪”(Adi)频繁出现在所有爱好体育的人们眼前——德国著名的运动用品公司“阿迪达斯”(Adidas),就是以其创始人阿道夫·达斯勒(Adolf Dassler)的名字命名的。
同样,有些植物的名字,也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在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植物的名字从先秦时代就频繁出现在各种典籍文献中,在这些名字之上积累的人文知识,也便如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
就拿桃子来说吧,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开始种植这种水果了。现在学界公认,桃树就是在中国得到驯化的。《诗经·周南·桃夭》的第一句就是“桃之夭夭”,本意是说桃花开得十分繁茂,后人却取了“桃”的谐音,把这句诗变成了“逃之夭夭”,意思也变为调侃人逃得远了。

|桃花,枝条上一个节生两朵花|
“桃花源”也是和桃有关的著名典故,出自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中,陶渊明描述了一个与世隔绝、安详宁静的田园世界,从此人们就把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叫作“世外桃源”了。
在《韩非子·说难》中则记载了弥子瑕分桃的故事:传说春秋时的卫灵公喜好男色,宠爱一个叫弥子瑕的人。有一天,二人同游果园,弥子瑕摘了一个桃子吃,觉得味道甘美,就把吃了几口的桃子递给卫灵公吃,给卫灵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后来,“分桃”就成了指代男同性恋的著名典故。
杏和桃是亲缘关系很近的水果,和杏有关的典故也不少。比如据说唐代诗人杜牧写过一首有名的七言绝句《清明》,后两句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虽然学界很多人怀疑这首诗是后世托名杜牧的伪作,但不管怎样,“杏花村”却因为这首诗成了酒家的代称。今天最有名的“杏花村”,自然是汾酒的产地——山西汾阳杏花村了。
东晋道士葛洪曾著有《神仙传》,里面记载了三国时吴国神医董奉的事迹。传说董奉隐居山林,每天为人治病,分文不取,只有一个条件:如果是重病患者被治愈,要在山上种杏树五棵,病不重的患者被治愈,则种一棵。这样过了几年,山上的杏树已经多达十万多棵,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子。自此以后,“杏林”就成了医学界的美称。

|杏花,枝条上一个节一般只生一朵花|
对于桃和杏这样的植物,虽然有着许多相关的典故,但其名字本身比较普通;而对于“远志”这样的名字,看一眼便觉得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了。远志是一种柔弱的小草,它的一个别名正是“小草”;但这样的一种小植物却被古人认为具有“益智强志”的威武药效,所以有了“远志”这个雄壮的大名。《世说新语》记载,东晋的谢安本来打算隐居不仕,还因此和不赞成他遁世的“书圣”王羲之发生过争执,可是耐不住朝廷几次征召,后来还是出来做了大将军桓温的手下。有一天,有人送给桓温几种草药,其中就有远志。桓温故意问谢安:“这种药又叫‘小草’,为什么会有两个名字呢?”谢安知道是揶揄自己,迟迟不作答,一边的郝隆嘴快,回答道:“在山里的时候是远志,出山就是小草了呗。”于是谢安面有愧色。不过,后来谢安指挥东晋军队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打败了前秦的进攻。这么看来,谢安出来做官,才真真正正是“远志”呢。

|远志|
然而,中文植物名(或者更严格地说是汉语植物名)也不过是世界上所有植物名称中的一小部分。其他语言中也有大量的植物名称,它们也都承载着大量的文化信息。这么多的植物名称固然是人类文化的宝库,却也给彼此的交流带来了很大困难。
比如马铃薯是原产南美洲的重要粮食作物。在汉语中,我们除了这个正式的名称外,习惯用“土豆”作为通称。此外,在不同的地方,它还有洋芋、洋山芋、山药蛋、地蛋、薯仔等名字,而《中国植物志》又管它叫“阳芋”。在别的语言中,马铃薯又被叫作potato(英语)、pomme de terre(法语)、Kartoffel(德语)、práta(爱尔兰语)、картофель(俄语)、ジャガイモ(日语)、 (朝鲜语)……所有这么多名字,指的都是同一种植物,这就是“同物异名”现象。
(朝鲜语)……所有这么多名字,指的都是同一种植物,这就是“同物异名”现象。

|马铃薯|
说到植物的同物异名,不妨在上面这个老生常谈的例子之外,再举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2012年7月,我从友人那里得知,新疆有一种叫作“雪菊”的植物,据说只长在天山山脉的高海拔地区,是新疆特有的、和雪莲齐名的珍贵野生植物。把它的花摘下来泡茶喝,据说可以调节三高、减肥养颜云云。起初我还真以为是什么稀有濒危植物,然而当我在网上看到雪菊的照片之后,却差点从椅子上跌倒——这不过就是原产北美大陆、作为观赏植物引种到中国的“两色金鸡菊”,在中国很多城市都有栽培。怎么它到了新疆,就被吹捧成“稀有高寒植物”“天山雪菊”了呢?

|两色金鸡菊/刘冰摄|
进一步的了解,更使我义愤填膺。从2010年起,一些不法商人开始炒作这种植物,很多农民便大量种植。然而到2012年,“雪菊”的炒作崩盘,价格一落千丈,很多农民收获的“雪菊”都卖不出去,损失惨重。这无疑是“同物异名”现象导致的一场悲剧——如果奸商们没有取“雪菊”这样一个不见经传的诱惑性名字,进而在其上编织“稀有高寒”的美丽谎言,如果人们都知道这种花叫作“两色金鸡菊”,它的英文名字是tickseed(直译是“蜱籽草”),那么这场炒作也就不太可能成功了。
其实,哪怕是去一趟超市,我们也能看到被称作“蛇果”的苹果,称作“奇异果”的猕猴桃,称作“提子”的葡萄,称作“车厘子”的大樱桃,称作“碧根果”的美国山核桃。当有些人一本正经地分辩说“提子不是葡萄”的时候,我们便再次看到给熟悉的事物另起陌生的名字所造成的巨大威力。

|猕猴桃|

|被称作“碧根果”的美国山核桃|
除了同物异名,自然还有同名异物。菩提树是佛教中的圣树,传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曾在印度一棵菩提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大彻大悟。然而,这种圣树是热带树种,在中国只能露天栽培于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省区。在靠北的长江流域,寺庙里只好用无患子树代替菩提树,却也管它叫“菩提树”。在更靠北的黄河流域,则用银杏充当菩提树。在青海的高寒地区(比如湟中的塔尔寺),连银杏也长不了,便只能用暴马丁香顶替菩提树了。这还不算完,现在的很多外语词典中,都把英语的lindenwood、德语的Linden、罗马尼亚语的tei、俄语的липа翻译成“菩提树”,于是搞出了“菩提茶”、“《菩提树》”(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一首歌曲)、“菩提树下大街”(德国柏林的一条大街)、“《菩提之恋》”(罗马尼亚的一首流行歌曲,后来被一位新加坡女歌手翻唱成“神曲”《不怕不怕》)之类的译名——然而这里的“菩提树”不过都是椴树的误译罢了。

|真正的菩提树(Ficus religios a) ,国家植物园温室栽培|

|暴马丁香(Syringa reticulat a )——西海菩提|

|苏格兰的『蓝铃花』——圆叶风铃草( C a m p a n u l a r o t u n d i f o l i a )|
在英语里面,bluebell (蓝铃花)则常常被作为同名异物的例子。在英格兰、西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和新西兰,蓝铃花分别指代不同的植物。当这些地方的人们唱起苏格兰民谣《苏格兰的蓝铃花》时,他们的眼前会浮现出自己熟悉的蓝铃花形象——而它们又都和苏格兰人眼中的蓝铃花完全不同!

|西非的“蓝铃花”——蝶豆(Clitoria ternatea)/刘冰 摄|
为了解决这些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的问题,在18世纪,瑞典非凡的博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von Linné,拉丁化的拼写则是Carolus Linnaeus,1707—1778)创立了直到今天还被植物学界奉为圭臬的植物命名法则。
植物命名法则的细节虽然很复杂,但它的基本原理很容易理解。林奈是用拉丁文来为植物命名的。拉丁语是古罗马帝国通用的语言,不过在林奈生活的18世纪,在民间已经没有人使用了。然而在那时候,不同的国家各自有不同的语言,有的还不止一种。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的学者为了能够相互交流,就只好继续使用拉丁语。林奈的绝大多数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所以他用拉丁文来为植物命名,也就顺理成章。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因为那时的拉丁语已经近乎死语言,再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变化了,所以用拉丁文为植物命名,可以保证命名系统的稳定性。
林奈对大多数植物物种都采用了“双名法”的命名方式。所谓“双名法”,就是用两个词来为植物命名,第一个词叫作“属名”,首字母要大写,可以视为植物的“姓”,第二个词叫作“种加词”,首字母通常都小写,可以视为植物的“名”。比如林奈给银杏起的名字是Ginkgo biloba,第一个词Ginkgo是“银杏属”的属名(来自日语“银杏”一词的拉丁转写),第二个词biloba则是银杏的种加词(意为“二裂的”,指银杏的叶片常常裂为两瓣)。
再比如桃的拉丁文名字是Prunus persica,第一个词Prunus是“李属”的属名,第二个词persica是桃的种加词,意为“波斯的”,所以这个名字直译是“波斯李”(当然啰,这个名字并不准确,因为波斯的桃终究是从中国传去的)。杏的拉丁文名字则是Prunus armeniaca ,第一个词也是“李属”的属名(也就是说,桃和杏“同姓”),第二个词意为“亚美尼亚的”,因为当时的欧洲人相信杏树起源于西亚的亚美尼亚地区。至于欧洲的李子(大名“欧洲李”,和中国的李子不是同一种),它的“姓”当然也是Prunus,“名”则是domestica,意为“家养的”,表明欧洲李是一种栽培植物。桃、杏、欧洲李的“姓”相同,同归为李属,说明它们具有相似的特征,在演化上具有共同祖先,正如同姓的人有可能“五百年前是一家”一样。
有时候,植物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同一属的两个种的亲缘关系没有原来想的那么近,便会为其中一个种“改姓”,把它挪到另一个属里面去。比如有的植物学家觉得桃和欧洲李差别不小,应该“分家”,于是把桃分到“桃属”Amygdalus里面,这样一来,桃的“姓”就由Prunus改成了Amygdalus。不过,它的“名”不变,还是persica,所以这时候桃的名字就是Amygdalus persica 。这些植物学家同时也觉得杏也应该“另立门户”,划到“杏属”Armeniaca里面,于是为它另起名Armeniaca vulgaris,其中的vulgaris意为“普通的”(之所以不叫Armeniaca armeniaca,是因为这个名字的属名和种加词拼写完全相同,而这种“重复名”是植物命名规则所不允许的)。当然,这种做法并不是所有植物学家都赞同。今天主流分类学界的共识是,桃、杏还是应该和欧洲李“联宗”,同归于一个广义的李属。
有了这种拉丁文的“科学名称”(简称“学名”),世界各国的学者交流起来就容易多了。比如马铃薯虽然有那么多的名称,但是学名就只有一个:Solanum tuberosum。那种被另外起名“雪菊”的北美植物,常用的学名也只有一个: Coreopsis tinctoria 。至于各种“菩提树”和“蓝铃花”,也都各有学名,不相混淆。曾经困扰人们的植物命名问题,便这样解决了。
植物的科学命名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烦琐的工作。学者们先要亲自采集或者派人采集标本(有时候甚至要冒生命危险),然后在标本馆中比对大量的标本,确定这些标本所代表的植物物种的范围和亲缘关系。接着,他们还要爬梳文献,找出相关的学名,如此才能为一种植物正确地定名。有时候,为了确定一种植物的正确学名,竟然需要几代人数十年的工作!
然而,作为对植物分类学家这种枯燥工作的奖赏,他们具有令人羡慕的为新植物命名的特权。他们可以用自己景仰的人、自己的良师益友甚至自己的爱妻娇儿(有时候也是自己讨厌的人)为新植物命名。新的植物学名一旦合格发表,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便不能被废除或代替,后来的学者只能老老实实地使用这个名字。于是,许多在史书中鲜有提及的人物,却在植物的学名中保留了自己的名字,并借此而不朽。除了人名,在植物学名中还能找到大量的地名、方言词等特殊词汇,它们无不携带着和植物相关的宝贵信息。
这样一来,植物学名也便承载了众多的历史和文化。看似冗长无趣的植物学名,其中往往蕴含着命名人的好恶,反映着植物学家的生平,甚至书写着一个国家的兴衰,折射着一个民族的气质。这些用拉丁文这种死语言的文字创造的名字,如果能够得以正确地解释和考证,便会成为信息丰富的史料,我们能够从中钩沉出一件件陈年旧事,不但可以匡补正史之缺,而且即便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也往往不输明星们的“八卦新闻”。
在这本书中,我将主要从中国植物的学名中挖掘有趣的故事。有些故事反映了西方人在中国采集植物的历史,是中国在历史上积贫积弱、国门为列强洞开的见证。有些故事反映了中国自己的植物学家艰苦创业、为摸清祖国植物资源的家底而奋斗不息的光辉历程。有些故事会让人扼腕叹息,或是令人捧腹大笑。此外,我也会讲述一些和植物的汉语名称有关的故事,希望这些故事同样能给读者有益的启迪。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活跃的一个时代。很多有关名字问题的论述,都是那个时代的哲人们给出的。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庄子说“名者,实之宾也”,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孔子还说过“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在劝勉他的学生学习《诗经》,夫子认为,《诗经》的一大功能,就是可以使人多认识动物和植物的名字。

|《诗经》的第一篇《关雎》就提到了名叫荇菜的植物:『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我想,我们不光要“多识”于草木之名,也要“多解”于草木之名。认识名字,是我们发挥万灵之长的智慧的第一步;而只有用心了解和体会名字背后的信息,才会让我们把外在的知识最终转化为内在的心灵体验,真正感受到精神生活的无上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