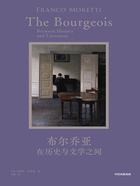
三、关键词一:“实用”(Useful)
11月4日。今天早晨我开始安排我的工作时间、带枪外出时间、睡眠时间和消遣时间。时间是这样安排的:如果天不下雨,每天早晨我带枪外出两三个小时,接着就干活到十一点左右,然后吃点东西,聊以果腹。从十二点到下午两点,我躺下睡觉,因这时天气极其炎热。然后到了晚上,我又重新干活。[1]
工作、枪、睡眠与消遣。但当鲁滨孙实际描述他的日子时,消遣消失了,他的生活使人能够丝毫不差地回忆起黑格尔对启蒙的清新明快的概括:在这里“,任何事物都是有实用的”。[2]实用:本书的第一个关键词。当鲁滨孙返回到海难之后的船上,文中那咒语般的重复——从木工用的箱子,“对我来说非常实用的收获品”,到“一些对我十分实用的东西”及“一切……可能对我实用的东西”[3]——通过把鲁滨孙放置在句子的中心(对我……对我……对我……实用)重新确定了世界的方位。同在洛克那里一样,这里的“实用”是这样一种范畴:它既确立了私有财产(对我实用),同时又通过将私有财产与工作结合起来(对我实用)而使之正当化(legitimate)。图里奥·佩瑞科里(Tullio Pericoli)为这部小说作的插图,看起来就像疯狂版百科全书的技术图样(图3,见右页)[4],却表达了这个世界的本质,在那里,没有物品自身就是自身的目的——在实用性(the useful)的王国里,没有事物是自身的目的——它们总是且只是做其他事情的一种手段。一个工具。而在一个工具的世界里,唯一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工作。[5]36

图3
一切事物都是为了他。一切事物都是工具。于是,有了实用性的第三个维度:
最后,由于我很想看看我这个小小的海岛王国的环境,我决定去游历一趟。于是我往船上为这次航行装贮食物,放上二十四个大麦面包(其实它们只是些饼),满满一陶罐烤脆了的大米(这是我平常吃得最多的食品),一小瓶甘蔗酒,半边羊肉,一些弹药(为了打更多山羊)和两件大值班衣——我前面提到过,这是我从水手的箱子里找出然后保存下来的;现在我带上它们,在夜里一件用来做垫被,一件用来做盖被。[6]
在这里,有作为故事行动中心的鲁滨孙(我决定……我装贮……我保存……我带上),有鲁滨孙远征所需的物品(陶罐……弹药……两件大值班衣),而紧挨着它们的,是一系列对于目的的解释——为这次航行……为了打更多……用来做垫被……用来做盖被,这三者共同完成了这个关于实用性的三角形。主语,宾语,和动词。一个动词已经内在地蕴涵着工具给人的训诫,它又在鲁滨孙的行动的内部对这重训诫进行了再生产:在那里,非常典型的是,做每一个行动都是为了做其他事情:37
因此,第二天我去了我那所谓的乡村住房,砍下一些小枝条,我发现它们正合乎我想要达到的目标。于是下一次我来的时候准备了一把短柄小斧去砍下大量枝条,我马上就发现,这种枝条这里多的是。我竖起它们在我的环形篱笆里晾晒,等晒干到适合使用时,我便将它们带回,放到山洞里,等下一个季节到来时,我就坐在山洞里使自己尽可能多地编一些篮子,来装土或是搁一些临时需要放的东西。虽然我编得并不漂亮,但却是十分适用的。这之后,我就注意到不让家里没有篮子,旧的用坏了,我又编新的,特别是我还编了一种又结实又深的大筐篮,准备等我收到大量谷物时来放粮食,再不用袋子装了。38
我费了许多时间克服这个困难之后,我又振作起来,看能够用什么方式来满足我的两种需求……[7]
每行两三个动词;如果换一个作家,如此之多的活动,或许会被写得狂乱不堪。但在这里,无所不在的目的论词汇(因此……想要……目标……准备……适合……使……适用……注意……满足)构成了一个缠结性的组织,使整页文字连贯、致密,而动词则以实用主义的方式把鲁滨孙的行动细分为主句中的直接的任务(我去了……我发现……我来……我竖起)与目的从句中的不确定的未来(去砍下……来装……来放……来满足);虽然可以肯定的是,这并没有那么不确定,因为对于实用性的文化来说,这个理想的未来,是一个就在眼前的未来,它不过就是当下的延续而已:“第二天”“下一个季节”“去砍下大量枝条,我马上就发现”。在这里,所有这一切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这些句子,没有跳过任何一个步骤(于是——下一次——我来的时候——准备了——一把短柄小斧——去砍下——大量枝条),就像黑格尔所说的“散文的心智”(prosaic mind),它们是通过“原因与结果,目的与手段这样的范畴”来理解世界的。[8]尤其是,目的与手段:目的理性(Zweckrationalität),韦伯将这样称呼它;以目的为指向的,或者说受目的支配的合理性(rationality);“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这是霍克海默(Horkheimer)在概念的变奏中所做的命名。在韦伯之前的两个世纪,笛福的文字所展示出的这样一种词汇——语法的联结,是工具理性的第一个化身:是还远未形成概念的,作为语言实践的工具理性——它被完美地表述,虽然完全无人关注。这是投向布尔乔亚“心性”的第一束目光,这是笛福给予布尔乔亚“心性”的伟大贡献:散文,作为实用之物的文体。39
[1]Defoe, Robinson Crusoe, pp.88-89.[译注]中文译文见丹尼尔·笛福著,唐荫荪译:《鲁滨孙漂流记》,第63页。
[2]G.W.F.Hegel,Phenomenology of Spirit,Oxford,1979(1807),p.342.[译注]中文译文见黑格尔著,先刚译:《精神现象学》,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46页。
[3] Defoe,Robinson Cruse,pp.69ff.[译注]中文译文见丹尼尔·笛福著,唐荫荪译:《鲁滨孙漂流记》,第43、47、50页。
[4]Tullio Pericoli,Robinson Crusoe di Daniel Defoe,Milan,2007.
[5]在这样一个工具的世界里,人类自身也成了工具-也就是说,仅仅是社会劳动分工中的齿轮;因此,鲁滨孙从来不用名字去召唤其他的船员,而只用活动:水手、木匠、枪手……
[6]Defoe, Robinson Crusoe, p.147.[译注]中文译文见丹尼尔·笛福著,唐荫荪译:《鲁滨孙漂流记》,第121页。
[7]Defoe, Robinson Crusoe, p.120.[译注]中文译文见丹尼尔·笛福著,唐荫荪译:《鲁滨孙漂流记》,第95页。
[8]G.W.F.Hegel,Aesthetics:Lectures on F ine Art,Oxford,1998,Vol.Ⅱ,p.974.[译注]中文译文见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