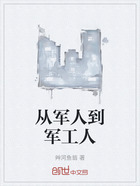
第20章 知青点
1977年初,微风中还带着丝丝寒意,四川石油勘探局的工作人员来到了黄瓜山上的永泸公路边,在紧邻我们大队茶山的那片地界上忙碌起来。他们不辞辛劳,一点点平整出一大块开阔的平地,随后又开始大兴土木。不久,一座由土墙和草房搭建而成的大院子,还有几排简易的工棚出现在眼前。在距离公路几百米远的山坡上,一个高大的钢铁井架也被稳稳地立了起来。为了方便运输通行,一条蜿蜒曲折的碎石公路,如同一条灰色的丝带,将井架与永泸公路紧紧相连。
春节前后,一辆辆载重卡车,载着川东泸州女子钻井队开上了黄瓜山,在新开辟的工地上,开始勘探天燃气。
这支钻井队,队员全是朝气蓬勃的青年女工。她们白天黑夜轮流上班,操作着各种设备,有条不紊地进行钻探工作。当我们在山沟这边生产队的地里劳作时,白天常常能听到山坡那边传来隆隆的机声,晚上看到灯火通明的工地上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远远望去,只见戴着头盔、手套,身着蓝色工作服的姑娘们,在飘扬的红旗之下,围绕着井架上下忙碌。
约莫数月之后,听闻在这片区域并未勘探到具备开采价值的气井,女子钻井队便悄然撤离了。曾经热闹非凡、喧嚣了长达半年之久的钻井现场,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只遗留下公路边那座草房院落,而曾经矗立着井架的山嘴,井架运走了,工棚也拆除了,变得光秃秃的,唯有一个围着栏杆的废弃井孔,井眼处还安装着一套金属装置,一股一人多高的火苗从那里蹿出,不分昼夜地燃烧着。这火焰一直持续燃烧到年底,才缓缓熄灭。
由于山嘴的地势相对较高,在那段公路上往来的车辆与行人,远远便能望见那跳跃的火焰。尤其是在夜晚,从地势较低的地方望去,那团火焰在黑暗中闪烁摇曳,显得格外醒目。
女子钻井队完成任务撤离之后,八角大队党支部经研究并请示公社后,决定利用女子钻井队留下的房屋,筹备建立大队知青点。国庆节刚过,我们大队的知青们便接到通知。除了几位已经结婚的老知青夫妇,出于种种生活考虑,继续留在原生产队生活之外,其余的13位年轻知青,包括7名男知青和6名女知青,便陆续从大队下属的各个生产队,搬入了位于大队茶场的知青点。
在集中到知青点的众人之中,若论起家乡的距离,我大概是最远的,来自繁华的重庆。而有一位女知青的家则是最近的,她来自黄瓜山山脚卫星湖畔的一个军工科研单位。另外11位知青,均来自永川县城。他们踏上下乡之路的时间都比我要早,最早的算起来,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七八年的时光。年龄稍长的,也已将近30岁。在仅有的两名不满20岁的知青里,我又是年龄最小的那个。
知青点是一座颇为宽敞的三合院,院子里的地面铺着三合土,看上去干净平实。男知青们住进了大门左侧的一排房子,而女知青们则安置在大门右面的那一排。正对大门的三间房子,布局也各有其用。最左边的一间被改造成了厨房,煮饭的炊烟天天从这里慢慢升腾;中间一间面积较大的,兼具食堂与会议室的功能,是大家的日常吃饭的地方,也是开会或学习的场所;最右边的一间则作为农具室和保管室,存放着生产生活所需的工具与物资。
钻井队修的这个院子房屋较多,因原是集体宿舍,每间的面积都较为宽敞。如此一来,我们每人住一间,竟然还有剩余的房间,这让大家都感到颇为惊喜。
知青们所携带的东西并不繁杂,除了一些必要的家具、农具,以及维持基本生活的日常用品外,主要便是粮食了。正因如此,搬家的过程显得格外简单。那时,我下乡已有一年多时间,国家供应的粮食早在两个月前就已到期。生产队分给我几挑谷子,还有一些小麦、苞谷和红苕,作为下一年的口粮。我将这些粮食全部搬进知青点,堆放在我那略显空荡荡的卧室一角。搬家的时候,生产队安排了几个小青年前来帮忙,大家齐心协力,仅仅两个多小时,便顺利完成了搬家任务。
知青点规定知青不单独开火,但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虽说大伙一同用餐,却也很难将其完全视作纯粹意义上的集体伙食,只是每个月由知青们轮流承担起煮饭做菜的任务,还是自己吃自己带来的粮食。
每天清晨,大家围坐在一起吃早饭时,会简单交流一番,统一意见,然后各自将当天要吃的大米,装在自己的大洋瓷碗里,送往厨房集中,由主厨的知青用蒸笼蒸熟。一般早饭和中午主要以大米为主食,晚上则是以麦粑、苞谷或是红苕为主。
在蔬菜方面,每个知青曾经自家自留地种的菜,都统一归为公有。负责掌勺的知青会一次性采摘一批,够大家吃上几天。这些菜被做成大盆菜,大家围坐在一起,共同分享。不过,有时候蔬菜不够吃,偶尔也会有知青到各个生产队的菜地里,悄悄摘上一些,只是具体是谁做的,一般没人过问。
没有新鲜蔬菜的时候,也不知是哪几位有心的知青,估计应该是女知青,搬来了好几个泡菜坛子安置在厨房。碰上没有新鲜蔬菜的日子,大家便会从坛子里抓出些泡咸菜,就着饭将就吃。
知青们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一起想办法改善伙食。经常有几个知青相约钓来鱼、抓来黄鳝或打来青蛙,另外的知青有的拿出自己的菜油、豆瓣等佐料,有的拿出烧酒,一起动手烹调一锅美食,大家一起享用。也有知青把自己回城从家里带来的鸡蛋、猪油或其它零食拿出来大家分享,知青点充满了其乐融融的和谐氛围。
下乡久了的老知青,也跟当地社员一样很少沾油腥,没有肉吃的滋味你莫说真的难受。有天黄昏,附近农民喂的两只大肥鸭,不知怎么跑进了知青点的厨房里来觅食。收活路回来的知青们见到后高兴坏了,赶紧关上大门把鸭子逮住。十几个男女知青半夜三更偷偷拿到坡上钻井队留下的那个点着火的井口,用我们捡的钻井队留下的一个煤油桶,把鸭子煮来吃了,打了一顿“牙祭”。丢了鸭子的那家女主人,对鸭子“失踪”的地点,凭直觉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她在知青点大门外爆了粗口,扯起喉咙破口大骂,要陪她“喂来下蛋的老鸭子”,但因为没有证据,闹了一个星期只好作罢。我因为独自嘀咕了一句隔靴搔痒同情失主的话,还受到大家一顿奚落。这就是拿人手软、吃人嘴软,真是自讨没趣。
知青点带来的不只是生活环境的改变,劳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兴许是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因素,黄瓜山上的茶叶和黄花梨都非常有名。知青点办起来后,大家也不回各自的生产队从事农业劳动了,统一在大队的茶场干活路,也协助果农管理果园里的果树,比较农业劳动而言轻松了许多。
知青点人数不算很多,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不同的成长经历,有不同的性格取向和不同的沟通方式。与分散住在生产队不同,知青们集中到一起后,年轻人思想活跃得多,性格也开朗,也谈得拢,没有一个人分散在生产队时的那种孤独和压抑。在顺坡的一梯一梯茶树间和另一条山沟的果树林里,集体劳动中少了生产队社员经常开的低俗玩笑,多了年青人的欢声笑语。大家也不计较分配活路谁轻谁重,争着抢着干重活。谁有个头疼脑热的小毛病,大家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令人心情舒畅。
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个微妙且敏感的变化,那就是刚刚由分散居住而聚在一起的知青们,人都不错,可虽然集中住进了一个院子,客客气气同吃一锅饭,热热闹闹同在一起干活,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可能是由于原来彼此不太熟悉,相互也不了太了解,大家同为知青条件相仿,心中都有个难解的结,似乎都有点不大情愿看到有人比自己先回城。这也是能够理解的,前因大概是前些年回城知青的示范,后果源自对未来的担忧与迷茫,这成为了朝夕相处中无法回避又必须回避的涉及切身利益的问题。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收工回来后大家往往关门闭户,一般来往不多,想找个人说话也不容易。
这种现象不可避免掩饰着某种排斥,为了回城而博弈初露端倪。何以见得?用法国作家蒙田的一句话来说:“世上任何一种利益,都是在损害他人的基础上得来的。”这话是说得绝对了一些,但它也道出了某种真实。
纵观历史,凡事讲关系是历朝历代流行的游戏规则,古代的士大夫官二代,在家庭的托举下,利用资源优势进行运作轻而易举;而大凡占有公共资源的实权派,或拥有人脉关系的能干人,可以轻松地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暗箱操作,实现个人愿望易如反掌;无关系可资利用的普通人,为了增加胜算,那就只能如老子所说的“将欲取之,必先予之。”通过歪门邪道如请客送礼拉关系搞交易,或者直接送钱行贿输送利益等等不正当手段,达到自己卑微的奢望。只能这么解释了。
想必这也是出于无奈吧。不过,集体生活中一旦出现了人情世故的某些弊端,那么对个体而言,执着的追求,理想的奋斗,便将失去它本来的意义。如此一来,调整与坚守,就成为了新的课题,“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大概就是针对这种情况的醒世恒言。
好在人际关系中保持一定的距离也不见得全是坏事,起码在客观上减少了一些矛盾与冲突。
到知青点后,只要周边的区、公社和石油管理局、军工科研所驻地单位等放映露天电影,知青们成群结队,再远都要去看。看露天电影不要钱,这一点特别招人喜欢;但往往要走很远的山路,这一点又讨人嫌。好在知青们为看电影都不怕苦,只要听说有电影看,我们知青和当地的年轻农民,经常收工后相互邀约,一大群人一起去看露天电影。大家有说有笑,边赶路边啃一个生红苕充饥或凑合吃两个梨子填肚子。每次看完电影,回来往往是深更半夜,虽然劳累,但很开心。
由于地处山地的地理环境所限,文峰公社在永川县是个比较小的公社,知青不多,且大都是永川县城的知青。除了知青点(本大队)和打篮球认识的几个其它大队的知青外,我还和公社两个喜欢读书的永川知青经常相互交换书来看,与公社其它的知青则交往不多。
在山下的公社,有个初中同学在河间区插队,我们在春节前相互到对方的公社进行了走访。还有建设厂的两个知青,他们有一个亲戚在文峰公社,他们在上山走亲戚时,到我的生产队来拜访过我。
农村的生活单调宁静,我们下乡第一年每月都有烟票和酒票,知青们平时生活沉闷,心情苦恼,男知青大都抽烟成瘾,也经常借酒浇愁。
重庆来的知青人数不多,分散在永川县的各个区,常常借赶场时碰头聊天,也在农闲时相约轮流到各自的生产队走访聚会,称之为“吃转转会”。
知青聚会除了粗茶淡饭吃顿饭之外,喝酒那是必不可少的。吆五喝六,划拳行令,闹到半夜,一醉方休。而后大家围着煤油灯彻夜长谈,往往你来我往,相互敬烟,在烟雾弥漫中吐槽日常生活的艰辛,分享放纵思想的快乐。这样一来二去,抽烟喝酒的陋习就更难改正了。
家住山脚石脚区的舅舅,每隔一段时间也要到翻过黄瓜山踏蹄沟煤矿挑煤,他挑煤时正好要路过我们知青点门口。每次他翻山去煤矿时,就会在去的时候给我打声招呼。我会加几把米多煮一碗饭,等他挑回来时,就在知青点吃了饭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