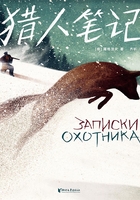
马林果之泉
八月初,热浪往往难以忍受。这个时候,每日正午到午后三点,哪怕是再坚定决绝的猎手,也不会外出狩猎;再忠实的猎犬,也只会“跟在主人的靴子后面转悠”。也就是说,狗儿们病恹恹地跟在身后,虚眯着眼睛,舌头夸张地耷拉着。主人要是责备它犯懒的话,它便低三下四地摇摇尾巴,一副可怜相,可就是不肯往前冲。
就是这么一天,我出门打猎去了。我纠结了半晌,很想找个阴凉地歇一小会儿。我那精力旺盛的狗子倒是在树丛里刨来刨去,尽管它自己看来也并不指望从这疯刨里获取什么。终于,在酷热的威逼之下,我不得不考虑保存我俩仅剩的些许力气了。我踉跄着来到已经向诸位好心的读者们提到过的伊斯塔河畔,下到河边,沿着湿黄的沙滩,往本地小有名气的“马林果之泉”走去。这眼泉,来自岸边。离岸边二十来步远的一道罅隙裂成了一截窄而深的沟子,泉水便从这里涌出,汩汩汇入河中。沟子旁长满了橡树,泉眼边冒出一小片光滑的草皮子,阳光几乎无法进犯它泛着银光的潮气。我来到泉边。草皮上有只桦树皮杯子,是谁放着给大家取水用的。我喝了个痛快,在阴凉地里坐了下来,环顾四周。
泉水入河之处,形成一个小小的水湾,永远泛着涟漪。水湾边上,两位老爷子正背对我坐着。其中一个高大壮实,身着整洁的墨绿长褂,戴着宽檐帽的,正在垂钓。另一位瘦瘦小小的,身着打了补丁的棉毛长襟衫,光着头,双膝间夹着一只盛满诱饵的陶罐。他不时用手捋捋灰白的头发,似乎是想保护脑瓜子不受暴晒。我仔细看了他两眼,认出他是来自舒米辛诺的斯乔普什卡。请各位读者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位人物。
离我的村子几俄里远的地方,坐落着一个叫舒米辛诺的村落。村里有座石质的教堂,是献给圣徒科西马和达米安注10的。曾几何时,教堂的周围喧哗热闹,聚集了各家地主宽敞的宅子。与此配套的,还有不少办公场所、手艺作坊、马厩、用来停放杂物或车马的棚子、澡堂子、临时食堂、客房、花棚、供民众游乐的秋千,以及其他场所,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宅子里住着本地阔气的地主们。他们原本过得不错。直到有一天,所有的这些场所被大火烧了个精光。地主们搬去了他处,这片庄园也就荒废了下来。大片的废墟渐渐变成了菜园子。星星点点夹杂在其中的,是断壁残垣和之前屋基的遗迹。人们收拾起尚未完全烧毁的原木,搭了一座小屋,用十年前买的本来是用来建一座哥特式厅堂的木板搭了顶,叫园丁米特罗凡和妻子阿克西妮娅带着孩子们住了进去。
主子命令米特罗凡向一百五十俄里开外的家里供应绿色蔬菜。阿克西妮娅呢,则需要照料主子花大价钱从莫斯科买回来的奥地利奶牛。自打被买回来后,这牛就没受孕过,因此也没产过奶。除此之外,她还得照料一只灰色的凤头公鸭,主子家唯一的家禽。孩子们年纪尚小,没被派什么活儿,也就彻底懒惰起来。我在米特罗凡家曾经住过两次,顺便尝过他种的黄瓜。天晓得咋回事,他那黄瓜,哪怕是夏天也长得老大,水分挺足,味道却不佳,皮黄且厚。就是在他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斯乔普什卡。除了米特罗凡一家和又老又聋、被一位士兵的寡妇收留在自家储藏室里的长老格拉西姆之外,舒米辛诺没有别的什么仆从了。因此,我要向各位读者介绍的这位斯乔普什卡,不仅算不上仆从,也许连个人也不算。
在这个社会中,任何一个人总有自己的位置、关系;仆从们就算拿不到工钱,至少主子们也得发点“辛苦钱”给他们。斯乔普什卡什么钱都没拿到过,跟谁都搭不上亲戚,没人知道他的存在。这个人仿佛没有过去,从没人谈起过他,人口普查好像都没查到过他。曾经有传闻说他什么时候当过谁的近侍,但他究竟是谁、来自哪里、父母何人,怎么成了舒米辛诺村里的奴才,怎么得到自己这件穿了不知道多久的混纺衫子,住在哪里、靠啥过活,—无人知晓,事实上,也没谁感兴趣。
特罗菲梅奇爷爷熟悉各家仆从家谱的点点滴滴。某次,他隐约道,这个斯捷潘注11好像跟一个土耳其女人有亲戚关系。那女人是已故的主子、当过准将的阿列克谢·罗曼内奇某次远征的时候带回来的。就算是过节的时候,当大家按照俄罗斯的传统,收到主子赏赐的荞麦饼和烧酒的时候,也从来见不到斯乔普什卡来到桌旁和酒桶前。他从没机会对主子行礼,没机会从主子肥胖的手里接过酒杯、在其注视下一口气干掉,并祝愿主子健康长寿。有谁同情他的话,大约会分一块没吃完的饼子给他。每年的复活节,大家还是跟他互吻祝贺的。不过,他却不会卷起油乎乎的衣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红色彩蛋,激动地屏息眨眼,递送到年轻的主子们或者是夫人跟前。
夏天,他住在鸡圈后面的小仓房里。冬天则在正房外间栖身,特别冷的时候,则在干草仓里过夜。大家都对他习以为常了,有时甚至会踢他两下,但没人跟他搭话,他自己似乎也从没发过声。大火之后,这个被抛弃的人住到了园丁米特罗凡家。按照我们奥廖尔人的说法,是赖在了别人家。园丁没招惹他,既没说“就住我这儿吧”,也没赶他走。
斯乔普什卡呢,也算不上是“住在”园丁家里,他是存在在那里罢了。他悄无影、静无声,带着点畏惧,咳嗽打喷嚏都用手遮着。他像蚂蚁一般,成天暗地里忙活着一件事—口粮。的确,要不是从早到晚地找食,斯乔普什卡非饿死不可。一早上起来,还不知道晚上能吃上啥,是多可悲呀!只见他不是坐在篱笆下啃着小萝卜、嘬着胡萝卜,就是抱着一棵脏兮兮的圆白菜掰着;要不就是呼哧呼哧把一大桶水往哪里拎着;或者还会生火煮一罐子水,并从怀里掏出一块块黑黢黢的东西往罐子里丢。他也会在自己的窝棚里干点“木活”,钉一只搁面包用的架子。这一切,他往往都是沉默地完成,就仿佛偷偷摸摸的,一被发现就要藏起来一般。有时候,他会消失一两天。当然,谁也不会察觉……再一看,他已经回来了,在篱笆旁边悄悄支了个铁架,生火煮着什么。他长着一张小脸,双眼泛黄;头发长得及眉毛,尖鼻子,一双大耳像蝙蝠一般透明;胡须就仿佛是两周前刚剃过,不见长长或者变短。在伊斯塔河边,我见到的正是这位斯乔普什卡和另外一个老头在一起。
我走上前去,打了声招呼,在他们身边坐下。斯乔普什卡的同伴我也认出来了。这位叫米哈伊洛·萨维利耶夫,外号图曼,是伯爵彼得·伊里奇家的自由人。他住在博尔霍夫一位患了肺结核的旅店店主家里。我是那家旅店的常客。行驶在奥廖尔的大路上的话,那些有闲心的青年官僚和其他人(不包括商人们,他们往往裹在毛褥子里酣睡)至今还能在离特罗伊茨克村不远的地方见到一幢庞大的木制二层楼。楼就建在路边上,早已是空屋一座,屋顶塌陷,窗户被封死。天气好的正午时分,这座空楼显得尤其黯然。这儿曾经是彼得·伊里奇伯爵的寓所。
伯爵是个好客的旧式大贵族。曾几何时,伯爵家往往汇集了全省的宾客,在家庭乐队高昂的伴奏和花炮声中、在罗马式的灯烛的照耀下载歌载舞。现如今,估计有不少老婆子经过伯爵旧宅门前,都要叹口气,怀念那已逝去的时光与青春。伯爵喜欢纵情吃喝,微笑着在各色宾客间踱来踱去。不过,他的财产可经不起如此挥霍一辈子。彻底破产之后,他去了彼得堡,想找份差事,还没等有结果呢,便在一间宾馆里溘然长逝。图曼原来是他家的看门人,在老爷在世时便获了自由身。这是个七十来岁的老头,长着一张标准而漂亮的脸。他仿佛总微笑着,且他那微笑是叶卡捷琳娜女皇时代式的,诚恳而威仪。说话时,双唇缓缓地张合,温存地眯着眼,多少带着点鼻音。吸鼻烟和打喷嚏,他同样是不紧不慢的,就像是在完成某项事业。
“怎么着,米哈伊洛·萨维利耶夫,”我问道,“钓够鱼了没?”
“您看看那网篮儿里呀,两条鲈鱼和五条雅罗鱼……斯乔帕,你给老爷看看。”
斯乔普什卡将网篮递来给我瞧。
“你过得怎么样,斯捷潘?”我问他。
“还,还,还可以,老爷,凑凑合合吧。”斯捷潘结结巴巴答道,仿佛舌头被什么给压住了。
“米特罗凡身体好吧?”
“好着哪,老爷,哪,哪儿能不好呢?”
可怜的家伙转过身去。
“咋不咬钩了呢,”图曼说道,“太热啦!鱼儿们都钻到水草里睡午觉去了……给钩子上个虫饵,斯乔帕。(斯乔普什卡拿出虫饵,放在手掌里拍了两下,钩在钩子上,吐了两口唾沫,然后递给图曼。)谢谢,斯乔帕……您哪,老爷,”他对着我继续说道,“是来打猎的咯?”
“你这不看到的吗?”
“好吧……我说您这只狗儿是应(英)国的还是方(芬)兰的?”
这老头儿逮到机会就爱自我显摆,展示他过往的见识。
“我也不知道是个啥品种,不过是条好狗儿。”
“这么说,您常带狗儿出行?”
“我有两队狗儿。”
图曼微笑了一下,摇了摇头。
“这不,有人爱狗爱得不行,有人呢,白送都不要。我想法简单,我觉得吧,养狗呢,主要是为了个身份……然后,一切都得井井有条:马儿们得被照料得好好的,狗舍也得井井有条,都得有个样儿!我们家老伯爵—愿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安息—从来就不爱打猎,狗却是养着的。一年两次也带着它们出来逛逛。到时候,养狗的仆从都穿上红色袍子,套上银带子,聚到院子里。喇叭一通吹,他老人家要出游啦!马儿也被牵过来,老爷要上马。猎手头头赶紧上前帮他把脚套进镫子,摘下自己的帽子,把马鞭放进帽子里递上去。老爷把鞭子一扬,养狗的们一阵大呼小号,便也跟着冲出去了。马夫得跟着伯爵呀,然后还得用丝绳牵着老爷最爱的两只狗、照料着……这马夫坐在高高的哥萨克式的鞍子上,满面红光,双眼圆瞪……当然啦,这种场合都会请客人来,既有趣儿又体面……嗨,这家伙居然挣跑了!”他突然插了一嘴,拽了拽钩子。
“这不都说伯爵这辈子没白活吗?”我问道。
老头朝虫饵吐了口吐沫,又把钩子甩了出去。
“大家都知道哇,我家老爷可是个大贵族。那彼得堡的头等人物也曾来拜访他呢,佩戴着蓝色的带子,围着桌子吃饭呢。当然,他老人家请客那也是毫不含糊的。往往就会对我吩咐:‘图曼,明儿我需要几只活的小体鲟,你叫他们给我捉来,听到没?’‘明白了,老爷。’他的那些成品袍子啦,假发啦,手杖啦,香水啦,上等花雾(露)水啦,烟盒啦,老大老大的画儿啦……那可都是从巴黎运过来的。这要是办一场宴会的话,我的个老天爷喂,这礼花可劲儿放,礼炮也得响。乐师一请就是四十来人。那指挥是个德国佬,可是不得了!想上主桌吃饭,就被老爷给赶跑了。他老人家说,我的乐师们没有他也能行。这就是主子的威风嘛。客人们要是跳起舞来,往往就跳到天亮咯,就爱跳那拉科谢兹和马特拉杜尔舞……哦哟哟,上钩咯!(老头子从水里钓起一条不大的鲈鱼。)斯乔帕,快装好了。老爷是个正经老爷,”老头子把钩子甩进河,继续说道,“心肠也是很好的。有时候敲打你几下吧,过阵子也就忘了。就有一点,他养了一帮子女人。老天,这都是些啥娘们儿啊!就是她们叫他破了产。他还总是从下等人里挑。对这些人还用得着咋地吗?那可不行,她们要的都是偶(欧)洲最好的玩意儿。就想放开了过好日子哟,地主爷的脾气……这不就得败家了吗?特别是有一个叫阿库琳娜的。她已经死掉了—愿她在天之灵安息!出身再普通不过了,西托夫村甲长家的女娃。脾气那叫一个坏!敢扇伯爵嘴巴子!把他给迷得神魂颠倒。我侄儿不小心在她裙子上溅了点热起(巧)克力,就被她命令送去当了兵……因为惹了她被送去当兵的可不止一个。可是呀,那还真是个好时候哟!”老头子深深叹了口气补充道,然后便垂下头沉默了。
“看来,你家老爷子挺严厉的?”我打破沉默问道。
“老爷,那个时候就兴这样。”老头摇摇脑袋,反驳道。
“现在可不这样了。”我盯着他,评论道。
他斜看了我一眼。
“现如今看来是更好咯。”他嘟囔着,将钩子远远甩开去。
我们坐在阴凉处,仍觉得憋闷不堪。滞重的热浪仿佛停住了。我举着发热的脸颊期待着凉风,风却迟迟不来。阳光从蓝得发暗的天空扫射下来。正对着我们的对岸上有一大片金黄的燕麦地,点缀着些许杂蒿,静得见不到一根枝叶晃动。再往下一点,有匹农家大马站在没膝的河里,懒洋洋地甩着湿漉漉的尾巴。伸出河边的灌木丛下,偶尔有条大鱼浮出水面,冒出一串泡泡,便又潜回河底,只留下阵阵涟漪。蝈蝈在晒得发红的草皮上吱吱叫着,鹌鹑们懒洋洋地哼唧着;只有鹰儿仍在田野上空滑翔,却也常常停歇一下,快速地挥动着翅膀,尾巴展成扇形。我们被酷热击垮了,静静坐着。忽然,身后的沟子里传来声响,有谁来到泉边了。我转身一看,发现一位五十岁上下的汉子,身着衬衫,脚趿草鞋,编织袋和毛料外套搭在肩上,风尘仆仆的样子。他靠近泉眼,一通畅饮之后站起身来。
“是弗拉斯吧?”图曼仔细看了看来人,喊道,“兄弟,这是哪阵风把你吹来啦?”
“你好呀,米哈伊洛·萨维利耶夫!”汉子边回应边走上前来,“我打远处来的。”
“你这是上哪儿去啦?”图曼问。
“我去了趟莫斯科老爷家。”
“做啥?”
“有事求他。”
“求啥子?”
“求他让我少交点钱,要不索性就把我招去服劳役、换个地方……我儿子没了,我一个人忙活不过来。”
“你儿子死了?”
“死了,不在啦。”汉子沉默了一会儿,答道,“他本来在莫斯科当车夫来着,替我交着代役的份子钱。”
“你们还交着代役的钱哪?”
“那可不?”
“主子怎么说?”
“能说啥?把我赶了出来。说,‘你怎么敢直接找上门儿来!不是有管事儿的吗,你有要求先去找管事儿的去……我哪儿有地儿给你换?你呀,’他说,‘先把欠的钱给我交上来。’他可真是生气了。”
“你这就回来了?”
“回来了。啥也没办成。儿子啥财产也没留下,也没成啥事。我跟他们头头说:‘我是菲利波夫的爹。’那家伙回道:‘我上哪儿知道去?而且你儿子啥也没留下,还在我这儿欠了钱。’我这不就回来了。”
汉子面带嘲讽讲述着这一切,就仿佛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不过,他那眯缝着的小眼睛里闪着泪光,嘴唇也抽动着。
“怎么,你现在这是往家走?”
“还能去哪儿?回家呗!老婆估计肚子正饿得咕咕叫呢。”
“你呀,我看得……”斯乔普什卡突然插话进来,然后又不好意思地沉默了,继续在罐子里翻着。
“不去找你们管家吗?”图曼继续问道,惊奇地看了看斯乔帕。
“找他干啥?……我这不还欠着钱吗?儿子死前病了一整年,自己的份子钱也没交……我都快愁死了,跟谁借去呢……兄弟,你呀,就别瞎出主意咯!就随它去吧!(汉子大笑起来。)他总是有点鬼主意,对吧,金其里昂·谢苗内奇……”
弗拉斯又笑了笑。
“怎么着?弗拉斯兄弟,我看情况不妙。”图曼下结论道。
“怎么不妙了?不……(弗拉斯顿住了。)这天儿真是热死人。”他用袖口擦了擦脸,继续说道。
“你家老爷是哪位?”我问。
“瓦列里昂·彼得罗维奇伯爵。”
“彼得·伊里奇的儿子?”
“彼得·伊里奇的儿子,”图曼答,“已故的彼得·伊里奇生前把弗拉索夫村分给了儿子。”
“他还活着?”
“上帝保佑,活着呢,”图曼接着说,“整个人红扑扑的,脸都横了。”
“我说,老爷,”图曼对着我说,“这要是在莫斯科附近,交代役也没啥。住在这儿怎么交得起?”
“得交多少钱呢?”
“九十五个卢布。”弗拉斯嘟囔道。
“您看哪,这儿耕地少得不得了,到处都是主子的林子。”
“林子据说早给卖掉了。”汉子补充道。
“您说说吧……斯乔帕,上个虫饵……斯乔帕?你睡着了还是咋的?”
斯乔普什卡猛地惊了一下。弗拉斯坐了过来。我们都陷入了沉默。对岸的某个地方,有人唱起了忧伤的歌子……可怜的弗拉斯真是愁得没法……
半个小时后我们便分开了。
注10 科西马和达米安为基督教圣徒,以慷慨好施著称,生活在公元世纪的小亚细亚地区。
注11 “斯乔普什卡”为斯捷潘的指小表爱形式。指小表爱是俄语口语里的一种爱称,一般用在长辈对晚辈、夫妻之间等比较亲密的关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