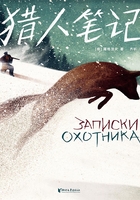
霍里与卡里内奇
有谁从博尔霍夫县去过日兹德拉县的话,很可能会对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差异感到惊奇。奥廖尔省的汉子个子不高,微驼,不爱直眼看人,住在破旧的白杨木屋里,服着劳役,不大爱做买卖,饮食粗糙,穿草鞋。卡卢加省交田租的汉子则往往住在宽敞的松木屋里,高大挺拔,看人的眼神直率欢快,脸色白净。他们从事着黄油和焦油的买卖,到了节假日还会穿起靴子。奥廖尔省的村子(我们在此说的是奥廖尔省东部),往往散布于开垦过的田地间,临近某个莫名其妙肮脏的水塘。除了几株稀稀拉拉、随意供人玩弄的爆竹柳和两三棵干瘪的白桦之外,周围就见不到什么像样的树木了。村里的木屋粘连在一起,还总是以烂稻草铺顶……相反,卡卢加的村落有林子环绕。木屋散落有致,且以原木板为顶。屋门锁闭严实,院篱紧密结实,不歪歪斜斜,以招致闲荡的牲口登门做客。就拿狩猎来讲,卡卢加省也更好。奥廖尔的林子和灌木丛再过个五年就会荡然无存,沼泽更是从来见不到。卡卢加省的林地则绵延不绝,沼泽往往一望几十俄里。美好的松鸡在此歌唱,憨厚的大鹬也常光顾,而那大大咧咧的山鹑往往猛地飞起,惊得猎手和猎犬们一个激灵。
我以猎人的身份造访了日兹德拉县。出了原野之后,我结识了一位叫波鲁德金的本地小地主。这个可爱的人也热衷于狩猎。他有那么些小弱点。比如,他几乎向全省的富家女子都提过亲,被女方本人和家庭拒绝后,他向自己的熟人朋友们长吁短叹,却还会给女子的父母寄去自家院子出产的酸涩的桃子和其他东西。他爱讲同一个笑话,尽管自以为深悟其幽默之处,却无法叫旁人发笑。他对阿基姆·纳希莫夫的创作赞叹不已,尤其是那本《平娜》。注1他有点口吃,给自家的狗取名为“天文学家”,把“不过”说成“不各”。按照他的指示,家里的饮食都是法式的。而在他厨子看来,法式烹调就是要完全改变食材自然的味道。经这位“匠人”的处理,肉带上了鱼腥,鱼则散发出蘑菇味,通心粉则莫名其妙带上火药味,而下进汤里的胡萝卜则必须事先切成菱形或者梯形。不过,除去这些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之外,就如上面提到的,波鲁德金是个大好人。
就在我跟波鲁德金认识的第一天,他便邀请我去他家过夜。
“到我家得有个五俄里吧,”他道,“走着去太远啦!我们先去霍里家吧。”(请读者们允许我不模仿他的口吃吧。)
“霍里是谁?”
“给我干活儿的……他住得不远。”
我们去了霍里家。霍里的木屋孤零零立在林间一块被彻底开垦出来的空地上。屋子由松木搭成,围有栅栏。正屋前搭有顶棚,由细柱支撑。我们进了屋。迎接我们的是一位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英俊挺拔。
“是费佳呀!霍里呢?”波鲁德金问道。
“霍里进城去啦,”小伙子微笑回道,露出洁白如雪的牙齿,“要给您备车不?”
“备车吧,伙计!再给我们上点格瓦斯。”
我们进了屋。洁净的原木墙上一幅苏兹达尔的木版画注2都没有挂。角落里镶银框的沉甸甸的圣像前,香炉微微燃着。刚打好的椴木桌子擦得干干净净。原木间和窗缝里见不到机灵的茶婆虫在游荡,也没有若有所思的小蠊爬来爬去。小伙子很快回来了,抱来一只大罐,盛满上好的格瓦斯。除此之外,他还拿来一大块面包和一大木盘酸黄瓜。他把吃食往桌上一放,斜靠在门边,微笑着打量起我们来。
我们还没吃完呢,门边便响起了车马声。我们走了出去。一个十五岁上下的鬈发红脸的男孩正吃力地拉着肥壮的花斑大马。马车旁立着六个青年壮汉,他们彼此很相像,而且都跟费佳长得很像。
“全都是霍里的娃!”波鲁德金道。“都是小霍里,”费佳跟着我们从屋里出来,接过话去,“这还没到齐呢:波塔普在林子里,西多尔跟着老霍里进城去了……瓦夏,你小心点儿,”他跟拉车的小男孩喊着,“跟紧啦!你这可是拉着老爷哪!颠簸的地方可得悠着点儿,别把车颠坏啦,把老爷颠吐了可不行!”其他的小霍里们都被费佳逗乐了。“让‘天文学家’也坐上来!”波鲁德金郑重吩咐着。费佳乐不颠地将勉强笑着的狗儿举起,放到了车底。瓦夏吆喝了一声马匹,我们飞驰起来。
“这曾是我办公的地方,”波鲁德金指着一处低矮的屋子,忽然道,“您想看看不?”“可以呀。”“它现在已经不是办公室啦,”他边下车边解释道,“不过还是值得看看的。”这曾经的办公处共有两间空屋子。看门人,一个独眼老头儿从后院跑上前来。“你好啊,米尼亚伊奇,”波鲁德金问候道,“给口水喝?”老头小跑而去,立马端回一瓶水和两只杯子。“您可得尝尝!”波鲁德金对我说,“这是我这儿的泉水,可口得很。”我们各自喝下一大杯,看门的小老头儿在一旁对我们深深鞠躬。“我们这就该走啦,”我的新朋友说,“就是在这里我卖了四俄亩的林子给商人阿里卢耶夫,得了个好价钱。”我们上了车,半个小时后便进了他的宅院。
“您说说看,”晚饭时候,我向波鲁德金问道,“为什么霍里跟您其他的佃农不一样,自己单干呢?”
“这是因为啊,他是个精明的爷们儿。二十年前,他的屋子遭了火灾。他来到先父跟前说:‘尼古拉·古兹米奇,请允许我住到您林子里的沼泽边上去吧。我会好好给您交钱的!’‘你这是为啥要住到沼泽地里去?’‘只是您呀,尼古拉·古兹米奇,就别再给我派其他的活儿啦!钱呢,需要交多少,您说个数儿就行!’‘一年五十卢布!’‘成,没问题。’‘你看好了哈,可不许给我藏着掖着!’‘怎么敢藏着掖着呢……’于是他就住进了沼泽地里。从那时起,人们就给他起了外号叫霍里注3。”
“他就这么发财了?”我问。
“可不就发了财吗?现在呀,他每年给我交一百卢布呢。我还得再加点儿。我都跟他说了多少次了:‘霍里,你就赎身了吧!赎身咯……’他呢,滑头,总是说没钱赎身……谁信他的呢!”
第二天,吃了茶点之后,我们又立马动身打猎去了。马车经过村子时,波鲁德金叫车夫停在一座低矮的屋子跟前,吆喝了一声:“卡里内奇!”“这就来啦,老爷,这就来,”院子里传来一个声音,“正在系鞋呐!”我们缓慢驶出村子。不一会儿,一个四十左右的高瘦的汉子追上了我们,不大的脑袋略微向后仰着。这便是卡里内奇。他那略带点麻子的忠厚黝黑的脸一下子就让我产生了好感。卡里内奇(我随后得知)每天都跟着老爷去打猎,帮他提着包裹,有时还扛着猎枪。他帮老爷观察,哪里有鸟儿停歇,给他找水喝、采果子吃、搭棚子,忙忙乎乎跑前跑后。没了他,波鲁德金简直寸步难行。
卡里内奇是个特别快乐温存的人,喜欢低声哼小曲儿,无忧无虑地四处张望。他说话带点鼻音,往往微笑着眯起淡蓝的眼睛,用手捋着刀片状的稀稀拉拉的胡子。他走路不快,用根细棍撑着,步子却迈得很阔。一天当中,他好几次跟我搭话,照顾得很周到却也没有巴结。当正午的燠热驱赶着我们四处寻找藏身之地时,他把我们带到了林子深处自己的蜂场。卡里内奇将我们引进一座由芬芳的干草束当窗帘的木屋,让我们躺在新鲜的干草垛上,自己则戴上头套,拿起刀、瓦罐和木块,去给我们切生蜜了。我们用泉水兑着透明温热的蜜喝了下去,在蜂子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沙沙的碎语中进入了梦乡。
一阵小风把我惊醒……我睁开眼,看见卡里内奇坐在半开的门槛上,正用刀子刻木勺。我久久地望着他如夜空般温存明亮的脸庞。波鲁德金也醒过来了。我们没有立即起身。长久的林间步行之后,躺在干草上特别舒服:身子松软开来,脸发着温热,甜蜜的慵懒叫人不想睁眼。最后,我们终于起身,并一直逛到了傍晚。晚饭时,我又讲到了霍里与卡里内奇。“卡里内奇是个善良的人,”波鲁德金道,“勤勉可靠的汉子。他倒是很能干农活的,却没法好好干。这不,我总拖着他天天陪我去打猎……您想,这还干个啥呢?”我很同意他的话。我们躺下睡去了。
第二天,波鲁德金得跟邻居皮奇科夫进城一趟,处理点不愉快的事。这位叫皮奇科夫的邻居在波鲁德金的地盘上忙活了起来,还在霸占了的地盘上打了他家的农妇。于是我一人动身去打猎,傍晚时顺便去了霍里那里。一位个子不高,秃顶结实的老头儿出门来迎接我。这便是霍里本人啦!我带着好奇将这位霍里打量了一番。他的脸叫人想起苏格拉底:高高的突起的额头,小眼睛,朝天鼻。我们一起进了屋。依旧是费佳为我们端来了牛奶和面包。霍里坐在长凳上,捋着卷曲的胡子,跟我聊了起来。看样子,他有充分的自尊,讲话和行动不紧不慢,偶尔从自己长长的胡子后面露出一个微笑。
我们聊了播种啦,收割啦,农民日常啦……他表面上是同意着我的话。之后我才反应过来,其实说了一堆不着边的东西……场面有点奇怪。霍里呢,看来是出于谨慎,有时并不直话直说。我们的谈话差不多就是如下进行的:
“我说,霍里,”我对他道,“你为啥不从老爷那儿赎身出来?”
“干啥要赎身哪?现如今啊,我既对老爷熟悉了,也对自己这块地儿适应了……我们老爷是个好人。”
“当个自由人注4不是更好吗!”我评论道。
霍里侧身看了我一眼。
“那是自然。”
“那你究竟为啥不赎身出去呢?”
霍里摇了摇头。
“我说老爷,你叫我拿啥子去赎哟?”
“得了吧,伙计……”
“霍里要是成了自由人,”他就像是自言自语低声接着说,“那些个不留胡子的都可以对霍里发号施令。”
“那么你自个儿就把胡子剃了呗。”
“胡子呀,胡子算个啥!还不就是一把草,说剃就剃。”
“所以说咯!”
“好吧,就算霍里经了商,商人的日子过得是不错,可不还是听人指挥的吗?”
“你本来不就做着买卖呢吗?”我问道。
“也就是卖点黄油和焦油罢了……怎么样,老爷,该不该给你备车了?”
“你呀,还真是个嘴严的滑头!”我暗自想。
“不啦,”我说道,“不用备车。明儿我想在你这园子周围转转。至于说今晚,要是你同意,我就睡在你的干草棚里啦。”
“欢迎!睡在干草棚里不会被吵到吧?我叫婆娘们给你铺上铺盖,备个枕头。婆娘们!”他边起身边叫道,“到这边儿来!你呢,费佳,跟她们去。婆娘们都挺蠢的。”
一刻钟后,费佳提着灯,引我进了干草棚。我扑进芬芳的干草的怀抱,猎犬在我脚旁趴了下来。费佳道了晚安,便将门吱呀关上了。我很久没能睡着。奶牛踱到了门旁,喘了两口气。狗子警惕地叫了起来。猪也哼哼着从旁边经过。近旁的什么地方,马儿嚼着干草,打着喷嚏……然后,我终于睡了过去。
清晨,费佳叫醒了我。这个欢快灵活的小伙子很叫人喜欢。据我观察,他也是老霍里的心头肉。他俩经常互相开开玩笑。老霍里向我走了过来。不知是因为我在他家过了夜,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霍里对我比昨儿亲切多了。
“茶点给你准备好啦,”他微笑着对我说,“一起去吃点吧。”
我们在桌边坐下。霍里的媳妇,一个壮实的女人端来一罐牛奶。他的儿子们鱼贯进了屋子。
“你这一大家高个子!”我对老头子道。
“是哦,”他边啃着一小块白糖边说,“对我和老伴儿,他们可没啥可抱怨的。”
“全都跟你一起住?”
“可不?他们自己乐意,这不就住着。”
“全都娶了媳妇?”
“那边那个,不就没成亲吗?”他指着像先前一样靠着门的费佳道,“瓦西卡还小,还可以再等等。”
“娶啥子亲?”费佳反驳道,“我这样挺好。要媳妇有啥用,跟她拌嘴不成?”
“你啊你……我可知道你!戴那么些个银戒指……你不就想跟那些女仆丫头们瞎混吗……‘够啦!不要脸的!’”老头子学着女仆们的口气,“我可知道你,你个游手好闲的!”
“婆娘有啥好的?”
“婆娘是干活的,”霍里郑重道,“是男人们的仆从。”
“我要干活的做啥?”
“你不就想靠别人吃饭吗?你这类家伙我可了解。”
“那你就给我娶个老婆呗。怎么样?咋不说话了?”
“够啦,够啦!就你会说!你看,我们都吵到老爷了不是。我啊,还就真给你娶个老婆……老爷,你可别生气。这孩子小,不懂事。”
费佳摇了摇头。
“霍里在家不?”门外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卡里内奇抱着一袋子草莓进了屋,这是他特意为老友霍里采的。老头子兴奋地问候了客人。我吃惊地望着卡里内奇。我得承认,我没想到,一个汉子能有如此“温柔”的举动。
这一天,我比平时晚了四个小时去打猎。接下来的三天,我都待在了霍里家。新相识令我兴趣盎然。不知道是什么使他们放下了防备,他们与我聊得轻松愉快。我饶有兴致地聆听他们的话,观察着他们。
这两个好友毫无相似之处。霍里是个积极稳妥、讲究实际的理性的人,擅长管理;卡里内奇则相反,属于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的行列,敏感而爱幻想。霍里对现实有充分的认识。他建起了屋子,积蓄也不少,与主子和其他有权力的人相处融洽。卡里内奇脚踏草鞋,日子过得马马虎虎。霍里生养了一个和睦而顺从的大家庭。卡里内奇倒是曾经也成过家,但他怕老婆怕得要命,也没能有孩子。霍里把老爷波鲁德金看得透透的。卡里内奇则对主子惟命是从。霍里喜欢卡里内奇,袒护着他;卡里内奇也爱戴霍里,对他充满尊敬。霍里讲话不多,总是笑笑,爱自顾自思考。卡里内奇爱热烈地讨论,却也不像那些兜售商品的贩子一般满嘴花言巧语……但卡里内奇有些天赋是霍里也认可的。比如,他能以咒语止血、压惊、驱魔;还是个养蜂能手,可算是心灵手巧。霍里当着我的面请卡里内奇帮他把新买来的马赶进马厩,卡里内奇郑重而认真地完成了这位爱怀疑的老友的请求。卡里内奇与自然靠得很近。霍里则擅长在人堆儿里混,是个社会人。卡里内奇不喜欢嚼舌头,对人都报以天真的信任。霍里则往往审时度势,甚至对生活不无嘲讽。霍里见识广,知道得多。我从他那儿了解到不少东西。
比如,他曾经讲述,每年夏天割草季前,总会有一辆模样新奇的马车来到各个村子里。车上坐着个人,裹着长衣,卖镰刀。要是付现金的话,他收一卢布二十五戈比注5;用现金券的话,则是一个半卢布;要是赊账,他会收三个卢布加一卢布银币。大家自然都是赊账。两三个礼拜后,他又出现了,这回是来收账的。大家刚把燕麦都割完了,当然也就有钱还债,于是就跟着他进了小酒馆,在那儿把债一一结清。有些地主就想自己用现金买些镰刀,然后再以同样的价格租给庄稼汉们。汉子们则颇为不满,甚至抑郁起来。他们喜欢自己挑选镰刀,用手弹弹刀刃,举着它试来试去,并跟滑头的商贩佯装抱怨:“怎么着,你这镰刀不咋地嘛!”差不多的情形也在小镰刀的买卖中出现。唯一的区别在于女人们往往会掺和到小镰刀的买卖中去,以至于有时惹得卖家对她们动粗,也是挺活该的。
不过,女人们在另外一种情形之下的遭遇更惨。本地造纸厂的供货商往往委托本县一些被叫作“鹰”的人去收购废旧布料。“鹰”从商人手里拿到两百卢布的现金券,便出发去寻找猎物了。与其绰号所指的雄武的鸟儿不同,这类人不会公开勇敢地发起进攻,相反,“鹰”使的是诡计。他把马车停在村边的某个灌木丛里,自己则进村挨家挨户沿着后院溜达,佯装过路的闲逛者。女人们隐隐猜到了他来的意图,凑上前去。一场交易便匆匆忙忙完成。仅仅为了几个铜板而已,女人们不单是卖掉了废旧衣物,常常还把丈夫的衫子和自己的毛料裙子也拿了出来。近些时候,女人们发现偷卖自家的大麻有利可图。这类举动被“鹰”们充分利用起来,成为他们扩展和完善自己的技艺的手段。因此,男人们可就警觉起来了。哪怕有一丝怀疑“鹰”的出现,他们便立即开始各类预警和防御措施。可不是吗,的确挺叫人恼火!卖大麻本来是他们的事呀!他们倒是不会卖到城里去,那不得自己进城吗?他们一般是卖给路过的商贩。由于没有秤,商贩们一般是按四十捧一普特计量的。您明白了吧,当俄罗斯汉子装“勤勉”的时候,他那“捧”得有多大!
这类故事呀,我这样从未在村里“待活”(我们奥廖尔省通常这么说)过的人,这下子可算是听了不少。不过,霍里不光是自己讲述,也问了我不少事情。当他听到我在国外待过,好奇心一下子就燃了起来。卡里内奇对此也颇有兴趣。不过,他更留意我对境外自然风景、山川水域、新奇建筑和大型都市的描述。霍里则关心行政和国家层面的问题。他一样一样问得非常仔细:“他们那边也是跟我们这儿一样的,还是其他什么样的?……你说呀,老爷!到底是啥样的?”“哇,老天呀,真有你的!”卡里内奇在我讲述过程中时不时感叹。霍里则沉默着,蹙着粗黑的眉头,仅偶尔评论道:“这个在我们这儿也没法实行,而这个却不错,很利索。”
我没法向您转述他所有的提问,也没有必要。不过,从我们的对话中,我得出一个结论,彼得一世是一个俄罗斯式的人物,尤其在他改革的过程中。这恐怕是读者们没有预料到的吧。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力量与坚韧是如此自信,甚至不惜自我摧毁,他不沉湎于过去,永远勇敢向前看。好的事物,他一律欢喜;有理有据的,他统统接受。至于这些事物的来源,他并不介意。俄式的积极态度对德式的冰冷理性来说,是个嘲讽。不过,在霍里看来,德国人是善于探究的民族。他乐于跟他们学习。
正是因为霍里独特的地位、实际上的自由身份,他打开话匣子跟我谈了许多。这要是别的什么人,可憋不出多少话来。或者按照男人们的说法,“半天也磨叽不出几个字”。他对自己的处境有充分认识。
在跟他的闲聊中,我见识到了普通俄罗斯汉子的智慧用语。他的知识算是广博的,却并不识字,没法阅读。卡里内奇是识字的。“这个家伙认得字,”霍里道,“养蜂子他也从没养死过。”“你送自己的娃儿们去识字了没?”霍里沉默了。“费佳识字。”“其他的不认识吗?”“其他的不认识。”“那是怎么回事呢?”老头子没直接回答,调转了话题。不过呢,再怎么聪明吧,他还是有他的偏见。比如,对女人们,他是打心眼儿里看不起。心情好的时候,总爱取笑她们。他的老婆,一个碎嘴的老太太,成天躺在炉炕上,翻来覆去,骂骂咧咧。儿子们并不大搭理她。媳妇们可都怕她怕得要命。这不,俄罗斯民歌里的婆婆总爱唱道:“你算哪门子我家儿子!年轻的媳妇儿你也不敢收拾……”有一次,我想替媳妇们说几句,试图引起霍里对她们的同情。他安详地回答我:“您管这些闲事儿干啥……就让婆娘们吵去吧……谁有那个闲工夫拉她们的架。”
老太婆时不时就从炉炕上下来,唤着看家狗:“狗儿,过这边儿来!”她用炉火钩敲打狗背。要不呢,她就站在门外的棚子下,像霍里形容的那样,对着来往的人“狂吠”。自己的丈夫,她倒是怕得很。只要他一发话,她立马钻回炉炕上去了。
不过,听霍里和卡里内奇聊主子波鲁德金则更为有趣。“我说,霍里,你可不许在我面前说他!”卡里内奇宣布。“哟,他可是连双靴子也不肯给你置备。”另外那位反问道。“我非穿那靴子做啥?我不就是个粗汉子吗……”“我也是粗糙爷们儿呀,可你看我穿的啥……”霍里一边说,一边抬起脚展示自己的皮靴。“你呀,跟我们又不是一类的!”卡里内奇答。“他要是给你点儿钱买双草鞋也行呀!你成天跟着他打猎,草鞋算个啥。”“他倒是给我买草鞋的。”“对哦,去年给过你一个十戈比来着。”卡里内奇沮丧地转过身去。霍里咯咯乐起来,眼睛眯成了一道缝。
卡里内奇善于演唱,三弦琴也弹得不错。霍里静静听了一会儿他的歌唱,然后把头弯到一边,扯起哀怨的嗓子,也跟着哼起来。他特别喜欢一首叫作《命哟,这就是我的命!》的歌子。费佳总是不放过机会,借此取笑老头子:“你这是装哪门子可怜哪?”霍里呢,则用手托着脸,闭上眼,继续哀叹自己的命……在平常的时间里,实在是没有比他更能干的人了,他几乎永远在忙活着:修理马车,整理篱笆,检查马具。不过呢,他对卫生倒并不大讲究。当我有天就此对他提意见的时候,他答道:“屋子里总该有点生活的气息嘛。”
“你看看,”我反对道,“卡里内奇的蜂场是多么干净呀。”
“老爷,蜂场要是不干净的话,蜂子可没法活。”霍里叹道。
“怎么,”有次他问我,“你也有自己的领地吗?”“有呀。”“离这儿远不?”“百十俄里吧。”“我说,老爷,所以说你在自己的领地上过咯?”“没错。”“多数时候还是打打猎取乐咯?”“这我也得承认吧。”“老爷哟,你就好好地多打几只松鸡,领地上的村长也勤换换吧!”
第四天傍晚,波鲁德金派人来接我了。我挺不情愿离开老头子。我与卡里内奇一起坐进了马车。“再见啦,霍里!你可得保重身体哟,”我道,“再见啦,费佳。”“再见啦,老爷,再见!可别忘了我们。”我们开路了。晚霞将天边染得通红。“明儿的天气一定不错。”我望着明朗的天,评论道。“不对啊,会下雨的,”卡里内奇反对着,“您看,鸭子们正扑通着,草味儿也太重了些。”我们的车驶进了木丛。卡里内奇低声哼唱起来,颠簸地望着天边的晚霞……
第二天,我便离开了好客的波鲁德金的家。
注1 阿基姆·纳希莫夫(—),俄罗斯讽刺作家。作品风格辛辣直白。《平娜》为其代表作之一。
注2 此类木版画是俄罗斯弗拉基米尔省苏兹达尔地区的特产,在俄罗斯民众间颇受欢迎,流行极广,其内容与形式也往往较为俗气。文中此处暗指霍里家的某种脱俗气氛。
注3 “霍里”在俄语里指艾鼬。
注4 此处指从原主人处获得自由身的农奴。
注5 卢布=戈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