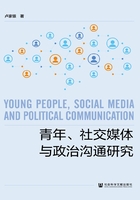
一 政治态度的理论检视
政治态度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心理现象,它与政治行为紧密相关,属于政治文化研究的范畴。所谓政治态度(political attitudes)是指公民对整个政治系统、政治系统中的各种角色、政治规制、政治系统中的输入与输出以及政治情境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4]这种倾向包括对政府机构、政治人物和公共政策等多个层面的内隐性和外显性评价。政治态度研究主要关注不同类型态度形成和改变的原因,常常将决定政治行为强弱的态度认知层面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对于政治态度的生成机制,学术界众说纷纭,有研究认为,政治传播中“经常出现的符号容易产生主导效果,所以政治态度的产生依赖于以往社会制约形成的记忆基础;也有研究者认为,政治态度的情感制约不受记忆的直接影响,但通常为一些粗略的符号所左右”。[5]同时,还有一些研究则认为从态度到行为的过程不是自动而直接的,一般而言个人在受到外在环境的刺激后,很可能会从记忆库里搜寻到相关政治信息,整理后形成政治态度。[6]
现有研究表明,影响公民政治态度的因素除了人口社会学范畴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等,媒介也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从报刊、广播、电视到互联网,每一种媒体的出现、发展和媒介新应用的扩散,都会对政治生活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作为民主社会运行的基石,大众媒体在形塑公众舆论、构建公共领域和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清末,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维新人士利用报刊启蒙新知、鼓吹变法,让变法思想“自通都大邑,下到僻壤穷陬”产生回响;孙中山、陈少白、宋教仁等革命党人通过报刊宣传暴力革命、推动社会变革,最终让革命主张深入人心。在现代社会,“通过政治组织和政治制度得以运行的政治体系,根本无法离开大众媒体的作用。大众媒体在设置政治议程、形成公共舆论、改变政治关系、影响公共政策、实施政治监督、塑造政治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7]对于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影响效果的研究已有许多,尽管不少研究都认为媒介使用和政治态度、政治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对时事新闻关注度越高,其政治参与度就越高,政治参与度越高,对时事新闻的关注度也会越高,但是迄今为止这种因果关系仍然是不确定的,尤其是快速发展的互联网。[8]
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在内容和形式上综合了传统媒体的各类特征,为公众参与公共政治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信息、技巧和平台,激发了参与的兴趣和意愿,具备推动公共参与和政治协商的潜能。威廉·艾威兰德(William P.Eveland)、克斯提那·马顿(Krisztina Marton)和迈亚·索伊(Mihye Seo)通过实验对比网络新闻的超链接和非超链接效果后发现,超链接网络内容与使用者的用户体验层级之间有明显的互动影响,对这类内容的消费,增长和丰富了复杂网络用户的政治知识,同时也影响了网络经验不足的初级网络使用者对政治知识的获取。[9]已有研究发现网络使用与政治态度、政治参与呈正相关关系。使用互联网越多也就意味着,在现实社会中拥有能够获得更多社会、政治网络资源的能力和权力。[10]布鲁斯·宾伯(Bruce Bimber)在研究互联网的政治功能时发现,尽管网络不会改变基本的多元化逻辑,但是网络能够减少草根群体动员和组织的阻碍,降低集体行动的成本,促进政治态度的形成。[11]对诸如脸谱和推特等社交网络媒体的使用,已经表现出与情境性政治参与有直接关联。[12]与专业媒体和职业记者的报道相比,对网络信息特别是用户自生内容的使用更有可能影响使用者的认知和态度。[13]
但是,对于互联网的政治影响,与前述乐观主义者的观点不同,悲观主义者的观点则显得比较谨慎。凯斯·桑斯坦(Cass R.Sunstein)告诫称,互联网不仅不会引起政治行为的重大改变,甚至有可能对公共政治生活造成伤害。[14]帕特南则指出,与网络使用率不高的民众相比,主要依靠互联网获取政治信息的民众,对公共政治生活的参与度较低。[15]毫无疑问,在互联网上花费过多时间用于观看和阅读任何材料必然意味着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与他人互动时间的减少。布鲁斯·宾伯(Bruce Bimber)对1996年至1999年间的网络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网络使用并未在社会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宾伯还发现,信息鸿沟的问题在互联网环境下还依然存在。他认为,互联网的大量使用将会导致信息和政治参与方面的鸿沟进一步扩大。[16]
对于青年群体,网络使用同样会影响他们对政治事务的看法。托马斯·约翰逊(Thomas J.Johnson)和巴巴拉·凯伊(Barbara K.Kaye)研究发现,青年网络用户不仅政治兴趣较为浓厚,而且表现出较高的政治效能。[17]穆罕默德·沙希德·尤拉(Mohammad Sahid Ullah)认为,青年人群对信息传播科技(ICT)的利用对公共参与具有重要影响,它提供了一个替代的信息交流平台,不仅有助于青年人群在虚拟世界表达观点(不论是不满还是焦虑),而且会影响青年人群对政治活动及决策的理解。[18]但是,也有研究者持不同主张。特拉姆·舒菲利(Dietram A.Scheufele)和马修·尼斯比特(Matthew C.Nisbet)通过研究指出,网络使用只对青年群体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具有非常有限的影响效果。网络信息搜寻与政治知识和政治效能并无多大关联,并且不能影响政治态度和参与。相反,传统媒体的使用却与政治知识、政治效能和政治参与存在更为强烈的相关关系。[19]
此外,媒介使用对公民政治信任、政治观念的作用还受媒介可信度的影响。媒介可信度反映了公众对媒体的信任和依赖程度,是媒介对公众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产生影响的重要基础。[20]一般认为,媒介可信度愈高,媒介使用频率会愈高,媒介对公众政治态度等的影响就会愈大。祝建华指出,民众对官方媒介的可信度越小,官方媒介的影响就越小。[21]廖圣清等人发现,受众对中国大陆传媒可信度的评价越高,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就越有信心。其中,受众接触媒介的频率、时间和获得的满足对受众的媒介可信度评价有显著影响。[22]对于传统媒体的可信度,廖圣清等人指出,目前我国电视的可信度略高于报纸和广播。与此类似,喻国明和张洪忠对电视、报纸、网络、广播和杂志五种传播媒介的可信度进行比较后发现,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电视的绝对公信力是最高的,其次是报纸和广播,最后是网络和杂志,但是广播、网络新闻和新闻类杂志都处于及格水平。[23]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的可信度略逊于传统媒体,但正在迅速提升。对于经济新闻、文教新闻和科技新闻,大学生群体倾向于相信传统媒介,而对于政治新闻、社会新闻、娱乐新闻等,他们更倾向于相信微博、新闻网站等数字媒介。[24]丛健认为,互联网的发展经历了大众从不信到半信半疑,再到相信,最后到完全依赖的过程。他指出:“在网络媒体发展的最初阶段,人们对于网上的信息并不相信,当时网络媒体的公信力水平是相对较低的。但随着网络的发展,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网络,他们看中了网络的方便、快捷、信息量大等特点,网络媒体的公信力也随之提高。”[25]基于以上文献讨论,本书做出以下研究假设:
H1: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频率与其政治信任度呈负相关。
H2: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频率与其社会公平感呈负相关。
H3: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频率与其民主意识观呈正相关。
H4: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对青年政治信任度(H4a)、社会公平感(H4b)、民主意识观(H4c)的影响与传统媒体的使用频率对三者的影响之间存在相互削弱的关系。
H5:社交媒体使用频率对青年政治信任度(H5a)、社会公平感(H5b)、民主意识观(H5c)的作用与媒介可信度对三者的作用之间存在相互削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