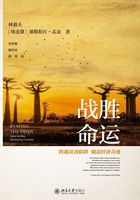
超越轶事的佐证:经济发展中的已知与未知
2002年,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正在准备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向他提出关于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和恐怖组织之间缺乏明确的联系这一问题,拉姆斯菲尔德依旧以他平时活泼的风格回应道:“我们知道,有一种知道的知道,就是有些事情我们知道自己知道。我们还知道有一种知道的不知道,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事情自己不知道。但是还有一种不知道的不知道——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其实自己并不知道。”[1]他的这一番话瞬间成为全球地缘政治词典的一部分,令人联想到孔子对于智慧的著名诠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2]
很显然,通过之前讨论过的三个经济上的成功案例,并不足以完整地归纳出有关经济发展的知识。它们可能只是提供了轶事证据和部分真谛,或许作为特别的历史叙述是有用的,但是要建立严格的经济理论,这些既不够全面也不够合理。[3]当我们要探索因果关系、搜寻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决定因素时,通常应该注意那些被忽略的变量的存在,包括“白噪声过程”(不相关的随机变量的随机过程),通过各种“已知”强加于理论推导之上的许多限制,各种“未知”,以及它们之间交互作用的神秘模式。又是这位拉姆斯菲尔德先生,当被问及为什么在推翻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控制了国家之后,美国军队仍无法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他回应道:“没有发现证据,不代表证据不存在。”这又是一个明智的观点陈述,它令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研究者无不同意。
众所周知,在经济学领域,理解并构成因果推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要清晰地阐述发展学理论也极富挑战性,这不仅是学术领域的严谨课题,对于每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也是非常有用的(获得明确的、积极的结果)。这便解释了一些专业领域内最有影响力的思想者在提供政策处方方面所表现出的不情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5年里,增长速度在7%以上的是13个治理方式迥异的经济体。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领导的增长委员会通过对这13个经济体的深度研究,确定了一系列与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相关联的典型事实:对全球经济开放,宏观经济稳定,高储蓄率和投资率,由市场配置资源,以及良好的领导力和治理能力。
但委员会很快得出结论:“我们不知道增长的充分条件。我们可以描述战后时期成功经济体的特点,但我们不能确定地说出它们取得成功的因素,也无法指出哪些是获得成功的非必要因素。如果情况正好相反就好了。尽管如此,委员们仍然敏锐地察觉到有一些政策可能至关重要——即使它们不能提供坚如磐石的保证,但是对于一个国家获得持续高增长的可能性会造成实质性的差别。正如我们不能说这个成分列表是充分的,也不能说所有的成分一定是必要的……一个成分列表不是一个处方,我们的列表也并不能构成一个增长战略。”(ComG 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2008,p.33)
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也是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被广泛认为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之父,但在讨论经济发展的谜题时依然十分谨慎。当被问及为什么经济学领域许多伟大的思想者往往回避详细阐述经济发展理论的挑战时,他解释说,这个主题实在太复杂了,不可随意轻言。而他自己的工作是致力于解释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特点,而不是提供一个经济发展理论。斯宾塞和索洛的谦逊确实令人仰慕。然而,寻找经济发展的秘诀至关重要,也正如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的名言所说的那样:“是不是有什么政府行动措施可以让印度的经济像印度尼西亚或埃及那样增长?”卢卡斯很想知道:“如果有的话,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使得印度如此这般的‘印度自身特点’是什么呢?这类问题涉及的人类福祉的结果是如此惊人:人一旦开始思考这些,便很难再做他想了。”(Lucas,1988,p.5)
本书承接卢卡斯的挑战,但是以不同于传统的方法穿行于一条求索真知的路途。从对于历史数据的观察入手,在工业革命之前,整个世界处于贫困之中(Maddison,2001),本书重点探寻的是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而如果纵观19世纪的英国、美国、日本,以及其他地方在工业革命之后和整个20世纪令人意想不到的经济成就,实际上,我们可以拼合出更大的图景和更完善的经济发展的知识图谱——经济发展总是出现在次优的环境中,这些地方并没有去实施那个冗长的结构性改革的清单。然而,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话语仍然提倡线性、目的论的经济发展路径,这对贫穷国家只能意味着困难重重,而并不能保证它们取得好的结果。
自柏拉图的 《泰阿泰德篇》以来,哲学家们一直在思索如何精准地定义什么是有用的知识以及如何得到它。他们的通用表述是“知识就是被辩明为真的信念”,也就是说,“相信什么是真实的,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对于发展领域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是没有实践价值的。许多研究者一直致力于阐述各种理论,他们认为,如果所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分析要具备严谨性、连贯性和有效性,就必须证明自己。
的确,脱离了其背后哪怕是隐含的理论基础,任何有关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都无以立足。正如Krieger(1976)对我们的提醒:“我们的选择不是介乎有一个理论或没有之间,因为我们必须得有一个(或两个,或三个,或多个不相容的)。我们的选择反而是,是否认识到那些理论不可避免地引发的批评,或者没有这样的认识,只是一味前行。”(p.7)但是,总还是要有一个界线,理论化的动力在跨越界线之后,只会带来越来越少的知识收益和越来越危险的认识混乱。[4]
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由理论霸权造成的问题已被广泛认识到(Sen,1977)。而当人们意识到“理论和假设是同义词”,而且“假设另外的同义词是假说、前提和推测”时,这些问题会变得更加尖锐(Manski,2013,p.11)。但是,研究人员的挑战努力可能已经走得太远。经验实证主义的兴起(通常认为是源于约翰。洛克的思想,洛克认为,一个人获得任何真正的知识,主要是通过实践经验,而现在则反映在对随机对照试验的广泛依赖上,并已成为发展研究的主要工具)也导致了对数字游戏内在价值的宗教式信仰。然而,这些所谓的以证据为基础的方法,往往是“马后炮”,项目分析的经验教训并不适用于其他领域,也不能对未来的政策选择提供预示,因为它们对政府规划有效性的预测能力并没有提升(Cartwright and Hardie,2012),结果往往会造成误导或产生无用的确信。
在本书中,我们选择了这样一种方法论的途径[5],借鉴经济理论的见解和经济历史的教训,采用一些经济分析与政策实践的经验。本书首先呈现了一个观察:如果各经济体的战略重点是基于其禀赋结构决定的显性的和潜在的比较优势,那么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环境下,技术的发展就可以使生产要素应用在最大化其回报和效用的地方,国家之间通过贸易活动而互利互惠。通过追随精心挑选的领先国家,落后国家可以充分发挥其后发优势,这种雁阵模式自18世纪以来帮助很多经济体实现了赶超。
这些观点体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方法,并基于Ricardo(1817),Gerschenkron(1962),Akamatsu(1962)等学者的见解,他们揭示了结构转型如何在社会、经济和体制条件不理想的环境中进行。对于拥有后发优势的落后的低收入经济体,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潜力甚至更大。此外,体量较大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如中国、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已经由低技能的制造业就业迁移到高薪资行业,这种经济上的成功和最终的“毕业”为低收入国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本书主张实施可行的战略,捕捉到这一新的工业化机会,这可以使低收入经济体步入一个结构变迁的动态路径,从而引领它们减少贫困,奔向繁荣。
本书其余部分的内容编排如下:第一至第四章对传统的发展学思想和虚设的前提条件提出挑战,认为解决发展问题的传统方法——专注于诊断诸多影响发展的障碍和限制,如“治理不善”、“人力资本不足”、“基础设施匮乏”——纯属误导。这些章节还指出,当前经济发展的主流观点所倡导的方法,即对于发展中国家仍然推行线性的、目的论的路径,会使政策制定——即使可能——也很困难,最后是将结果交于随机性和偶然性。认为旨在改善贫穷国家“治理”和商业环境的结构改革可以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从历史和概念的角度来看都是不现实的。缘于何故?这种方法是以高收入国家拥有的或高收入国家做得相对较好的地方作为参考,用以确定一个发展中国家所缺乏的或做得不好的方面。然后,他们建议发展中国家争取得到高收入国家所拥有的东西,或者做高收入国家所做的事情。这种方法往往没能完全考虑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在发展先决条件上的差异。
第五至第七章列举了实现高增长的具体措施,即使是在制度和商业环境不利的贫穷国家,只要着眼于已有的基础,着手于自身擅长的方面,同样可以做得很好。如果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拒绝接受那些强调先决条件的决定论,取而代之以加大对本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促进力度,政府就可以利用其有限的资源和实施能力进行战略性规划,在工业园或特区内营造一个良好的地方商业环境,那么,可以说所有的低收入经济体就都可以实现包容性的高增长。要问制胜战略的主要成分配方是什么,那就是选择具有竞争潜力的产业,致力于推进破坏性最小且回报率最高的改革。
[1] 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于2002年2月12日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
[2] 出自 《论语。为政》。——译者注
[3] 至少在大卫。休谟之后,因果分析和因果推理已经在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风靡起来。参见Hoover(2001)针对这方面主题的主要思想的精彩评价.
[4] Kavanagh(1989)的观点与文献理论有类似之处,Kavanagh指出,“极限”一词应该在数学意义的背景下理解,是指超越某一个临界点会发生变化,在这一界线之外,一个事物成为另一个的质变情况就将发生.
[5] 本书的理论基础见于两位作者之前的一些作品(Lin,2012a,2012b,2012c;Lin and Monga,2013;Monga,2014).